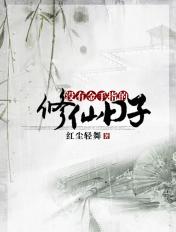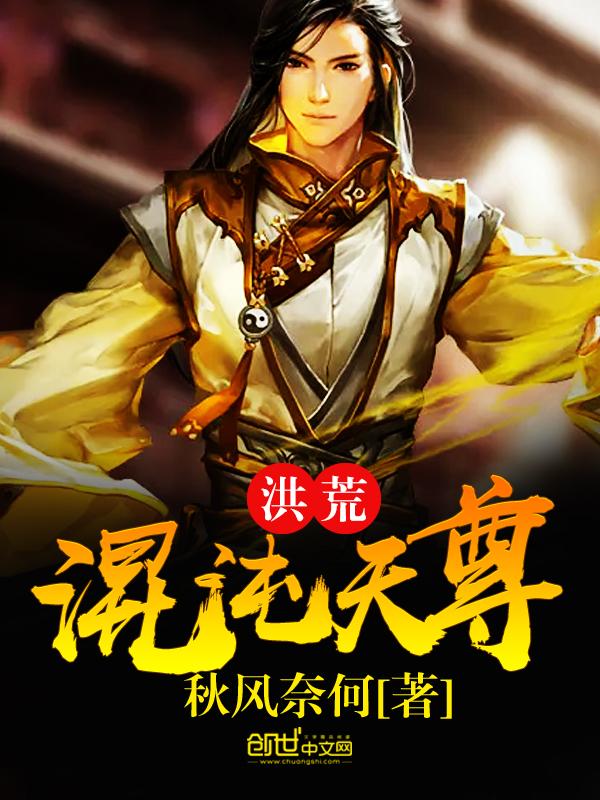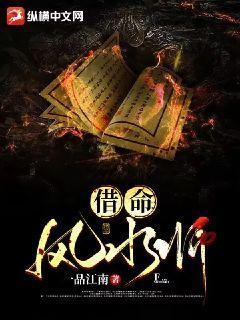鹅绒锁>全家夺我军功,重生嫡女屠了满门 > 第625章 许靖央写奏折 自请离京(第1页)
第625章 许靖央写奏折 自请离京(第1页)
朝堂风云骤变。
就在赵曦伏诛七日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率先上奏,以“东宫曾举荐赵曦参军”为由,质疑太子识人不明。
这道奏折如同投入静湖的巨石,瞬间激起千层浪。
紧接着,刑部侍郎呈上一份密报,揭露赵曦在牢狱中的时候,曾极力要求见太子。
虽然狱卒证词模棱两可,但经有心人渲染,竟成了太子与赵曦往来的铁证。
更有人翻出旧账,指出太子曾在钦天监说出福女天象的时候,称赞赵曦“福女之说可信”,如今看来竟是别有用心。
风雪夜,灯塔第一百盏长明之火在云层中劈开一道金线,直贯天心。许明烛立于塔顶,手中紧握那份《玄螭会成员名录》,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名单上的名字如毒蛇盘踞,缠绕着大胤江山二十年,吸髓啖骨,如今终于暴露于光下。
她没有犹豫。
“焚鳞计划”,即刻启动。
第一夜,礼部尚书暴毙府中。死状诡异??七窍流血,面带惊惧,唇齿间竟含一片烧焦的鱼鳞。府邸内外无丝毫闯入痕迹,唯书房案上留有一封密信,墨迹未干:“五十七已查,双鱼归位。”影舵回报,此人曾收受黄德全贿赂三万两,篡改西疆战报,将阿荼之功记于许敬之名下。他至死不知,那笔银子的每一枚铜板,都沾着边军将士的血。
第二日清晨,工部侍郎在上朝途中坠马,颈骨断裂。可苏砚亲自验尸,发现其耳后有细微针孔,乃“牵机引”微量注射所致,发作时使人筋脉失控。此人掌管军械调度,曾克扣寒衣十万件,致使北境守军冻毙八百余人。他死后次日,家中妻妾争产内斗,撕开层层锦被,竟从褥底搜出一卷写满供词的绢布??是昨夜有人潜入,逼其亲笔写下罪状。
第三日,大理寺卿称病不朝。许明烛冷笑:“他怕的不是病,是影。”
当夜,大理寺档案库突发大火。火势猛烈,却只焚毁了永和五十六年至六十年的刑案卷宗,其余毫发无损。火场残骸中,发现半枚带血玉佩,经辨认为当年主审阿荼“通敌案”的佐证官遗物。该官早已失踪多年,传言被灭口沉江。而今,他的冤魂似乎也借火鸣冤。
京城人心惶惶,官员们开始互相猜忌。有人闭门谢客,有人连夜遣妾出城,更有人跪拜佛堂,焚烧往昔书信。可恐惧无法洗清罪孽,唯有供述能换一线生机。
许明烛不动声色,命影舵广布耳目,凡有异动者,皆录其行踪。她要的不只是七人之命,而是整个玄螭网络的崩塌。
与此同时,雁门关外石窟所出九具铁匣,已被秘密运抵灯塔地宫。许明烛亲自开启第一匣,内藏《永和实录?原始功勋录》,纸页泛黄,字字如刀。她翻至西疆战役篇,指尖停在那一行铁铸般的名字上:
**“镇国大将军阿荼,斩敌八千,平三十六部,功居第一。”**
而在其下,赫然标注副将九人姓名,皆为“双鱼盟”旧部。其中一人,竟是她父亲许正清!
原来,父亲并非只是追查玄螭会的御史,而是阿荼麾下第七营统制,代号“青梧”。他在战后察觉军功被篡,愤而上书,却被反诬勾结叛将,贬谪岭南。临行前,他将兵符与密档托付一名亲信送往边关藏匿,自己则孤身赴死,只为保全女儿性命。
许明烛跪坐于地宫石阶之上,捧册无声落泪。二十年来,她一直以为父亲是因直言进谏而亡,却不料他是背负着整个忠良集团的秘密赴死。他不是失败者,他是最后的守夜人。
“父亲……”她低语,“我接住你扔出的火把了。”
就在此时,地宫深处传来一声轻响。
苏砚疾步而来,神色凝重:“大小姐,最后一匣……打不开。”
那是一具通体黑铁铸造的匣子,比其余八具更小,却重达百斤,四角嵌有青铜锁钮,中央刻着一行古篆:**“非血不可启。”**
许明烛抚过铭文,忽然想起什么。她取出发簪,划破指尖,将血滴于锁心。
“咔??”
一声闷响,铁匣应声而开。
里面并无文书,唯有一面铜镜,镜背镌刻双鱼交尾图腾,镜面却漆黑如墨。她怔了一瞬,忽觉一阵寒意自脚底升起。镜中缓缓浮现出影像??
一间幽暗密室,烛火摇曳。几名黑袍人围坐圆桌,头顶悬着一盏琉璃灯,灯焰呈诡异青色。他们皆戴面具,形制各异,唯居中一人,头戴金鳞冠,背影熟悉至极。
那人缓缓转身。
许明烛呼吸骤停。
那是当今圣上。
不,准确地说,是**长得像当今圣上的人**。
真正的皇帝,此刻正被囚禁于某处?还是早已……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