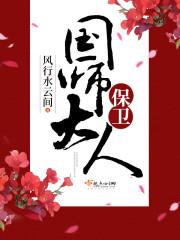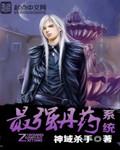鹅绒锁>没钱怎么当明星 > 第二百四十三章 怎么感觉处处是商机啊(第1页)
第二百四十三章 怎么感觉处处是商机啊(第1页)
巨人的坍塌总会给后人带来无数的反思。
玄机现在发展虽然还算健康,但确实面临着严峻的发展困境,步子大了怕扯到蛋,步子小了怕跟不上,左右为难啊。
“埋头做内容的企业就会面临这种情况,因为不符合。。。
林小树在天台敲完最后一行字,合上电脑,风比清晨更冷了。他把卫衣拉链拉到下巴,望着远处CBD的霓虹灯群,像一片永不熄灭的星河。这座城市从不缺光,可真正能照亮人心的,从来不是这些。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黄圣衣发来的消息:【我爸看了《大地之音》回放,哭了。他说,你比他自己更懂他。】
林小树笑了笑,指尖在屏幕上停了许久,才回:【因为他本来就很了不起。】
他刚想收起手机,又一条信息跳出来??王曜:【联合国那边临时调整议程,《普通人之声》主讲人环节提前至今年九月,纽约站开幕式压轴出场。主办方说,他们希望“那个跪在父亲脚下的中国青年”亲自讲述“声音如何改变命运”。】
林小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
他知道,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演讲,而是一次文化的出征。他代表的不再是某个节目、某部纪录片,而是千万个沉默却未曾屈服的灵魂。
他回了个“收到”,然后拨通李春梅的电话。
“我要去一趟云南。”他说,“‘嘎老’合唱团的老人们答应参加纽约巡展现场演出,但他们年纪太大,没人敢担保行程安全。我想亲自去接他们。”
李春梅沉默了几秒:“你确定要现在走?《我在》第十集正在剪辑,媒体都在等你回应最近的争议。”
“什么争议?”
“有人发长文质疑《大地之音》是‘悲情营销’,说我们利用贫困博同情,甚至称你是‘新时代的民粹偶像’。”
林小树轻轻叹了口气:“让他们说吧。真相不在键盘上,在路上。”
第二天一早,他背着双肩包登上飞往贵阳的航班,转车六小时抵达侗寨所在的黎平县。山路蜿蜒,雨后泥泞,车子颠簸得像在跳舞。司机是个本地年轻人,一路上絮絮叨叨:“你们城里人总说我们穷,可你们来拍我们唱歌的时候,眼睛都是亮的。我奶奶说了,歌还在,魂就没丢。”
林小树听着,没说话,只是默默记下了这句话。
傍晚时分,他站在寨门口,木楼错落,炊烟袅袅。八位老人早已被家人搀扶着坐在火塘边等他。最年长的吴阿婆九十二岁,耳朵几乎听不见,但听说“小树来了”,硬是让人给她梳头换衣,戴上祖传的银项圈。
“你来了。”她用侗语说,由孙女翻译,“我们一直在练,怕到了外国,唱不好。”
林小树跪坐在她面前,握住她枯瘦的手:“您唱的每一个音,都是历史在呼吸。”
那一夜,他们在火塘边喝了米酒,吃了腌鱼,听老人们一句一句复述古歌的含义。那些歌词讲的是祖先迁徙、洪水滔天、稻种如何从天上落入人间。没有一句提到苦难,却处处藏着坚韧。
“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人可怜。”另一位老人石大爷说,“是为了告诉后代,我们走过来了。”
第三天,林小树带着团队开始录制送别视频。他没让摄影师摆机位,只用手机拍下老人们收拾行李的模样:有人把族谱缝进布包,有人带上了陪伴一生的牛角号,还有人坚持穿民族服饰,哪怕坐飞机不方便。
临行前夜,全村人聚在鼓楼下为他们送行。孩子们跳起芦笙舞,老人们齐声唱起《离别调》。歌声一起,林小树眼眶就红了。
他忽然起身,走到鼓楼中央,掏出随身携带的口琴,吹了一段《我们的字典》主题旋律。那是他在“微光班”教孩子们的第一首曲子,简单,却有力。
老人们听懂了,随即改调接入侗族大歌的和声体系。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在这一刻自然融合,仿佛山川与河流交汇。
视频后来被上传到“原生记忆实验室”账号,标题只有四个字:《出发》。
播放量破亿,评论区刷屏:
>“这才是文化输出。”
>“他们不是去表演,是去回家。”
>“请全世界听听,什么叫活着的声音。”
一周后,八位老人顺利抵达北京,在国家非遗中心进行适应性休整。林小树每天早晚都来探望,陪他们散步、吃饭、试音。医疗组全程跟进,心理辅导师也随时待命。
但他发现,最让老人们焦虑的,不是身体,而是语言。
“我们不会普通话,更不会英语。”吴阿婆担心地问,“外国人听得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