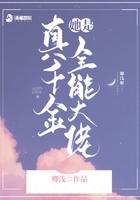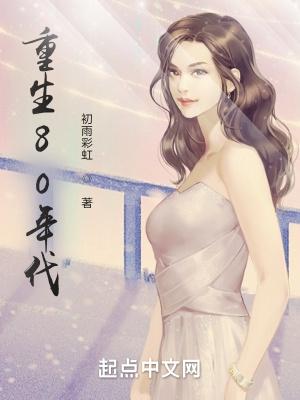鹅绒锁>坐看仙倾 > 第401章 同样的灼热气息(第3页)
第401章 同样的灼热气息(第3页)
忽然,风停了。
一道模糊的身影出现在镇口,披着黑色斗篷,面容隐藏在阴影之下。他手中握着一块碎裂的玉符,正是当年烬渊遗留之物。
他没有说话,只是抬手一挥,四周温度骤升,冰雪融化,屋舍自动修复如初。随后,他在每户门前放下一小袋粮食与药材,悄然离去。
有人追出去想道谢,只看到雪地上留下的一串脚印,延伸向远方,尽头处,隐约浮现出一座虚幻宫殿的轮廓??凌霄殿。
“是他……”一位老人喃喃,“那个被世人遗忘的守护者,回来了。”
而这道身影,正是融合后的季忧所分出的一缕化身。他不再逃避黑暗,也不再压制愤怒,而是让那部分情绪有了自己的形态与使命:**专行隐秘善举,救急难而不留名,承怨气而不报复。**
这才是真正的“圆融之境”。
时光流转,十年倏忽。
这一年春分,观微里槐树下再次亮起点点灯笼。
村民们围坐一圈,吹响柳笛,唱着自编的小调:
>“青衣人,行路长,
>踏遍山河送暖阳。
>不求仙,不炼丹,
>只愿世间少凄凉。”
忽然,天空星辰再次异动。
文曲星光芒大盛,竟分裂出九道分支,分别投向九个方向:西域、东海、南疆、北漠、中原、蜀山、苗岭、阴山、昆仑。每一束星光落地之处,皆有一座学堂拔地而起,名为“观微书院”。
这些书院不收束?,不论出身,凡愿修《太初正典》者皆可入学。教材并非艰深法诀,而是教人识字、算数、耕种、医病、调解纠纷……并将“孝、仁、信、敬、悯”五德融入日常言行考核。
十年之内,九院共培养出三千六百余名“平民修士”,他们不追求飞升,也不参与宗门争斗,只在各地担任教习、医师、匠师、巡防使,默默构筑起一个新的秩序。
有人问:“这些人算不算仙?”
一位老学者答:“若仙是指凌驾众生之上者,则他们不是。
但若仙是指明知世道艰难,仍选择点亮灯火的人??那么,他们每一个,都是活着的神仙。”
又过了二十年。
季忧的名字渐渐从官方史书中淡去,只存在于民间歌谣与孩童睡前故事之中。
但在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南方一座小山村突遭山洪冲击。河水暴涨,桥梁断裂,数百村民被困高地,命悬一线。
救援迟迟不到,绝望蔓延。
就在这时,一位背着竹篓的老药农冒雨赶到,指挥众人用藤蔓编织浮筏,又点燃三堆大火指引方向,最终协助官府成功营救全部灾民。
事后有人问他姓名。
老人笑了笑,从怀中掏出一支磨损严重的柳笛,轻轻吹了一小段旋律,然后转身走入雨幕。
那一夜,许多人都说,听见了熟悉的笛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从心底响起。
而就在同一时刻,天际某颗本已黯淡的星辰,微微闪了一下,仿佛回应某种久别的召唤。
多年以后,一位年轻的观微书院学子在整理古籍时,发现了一份残卷,上面记载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对话:
??当年季忧完成《太初正典》后,曾有人问他:“若天下皆修此道,人人向善,是否便可永保安宁?”
他摇头:“不行。人性有光,也有暗。善不能消灭恶,只能让它无处藏身。真正的太平,不是没有风暴,而是风暴来临时,总有人愿意站出来,为别人挡住一阵风。”
学生读至此处,久久不能言语。
窗外春雷滚滚,新芽破土。
他提笔在卷末添上一句:
**“坐看仙倾者,非不动心,而是心虽千疮百孔,依旧选择相信春天。”**
墨迹未干,屋外忽有清风拂入,卷起纸页,绕梁三圈,又轻轻落下。
仿佛有人曾在此驻足,颔首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