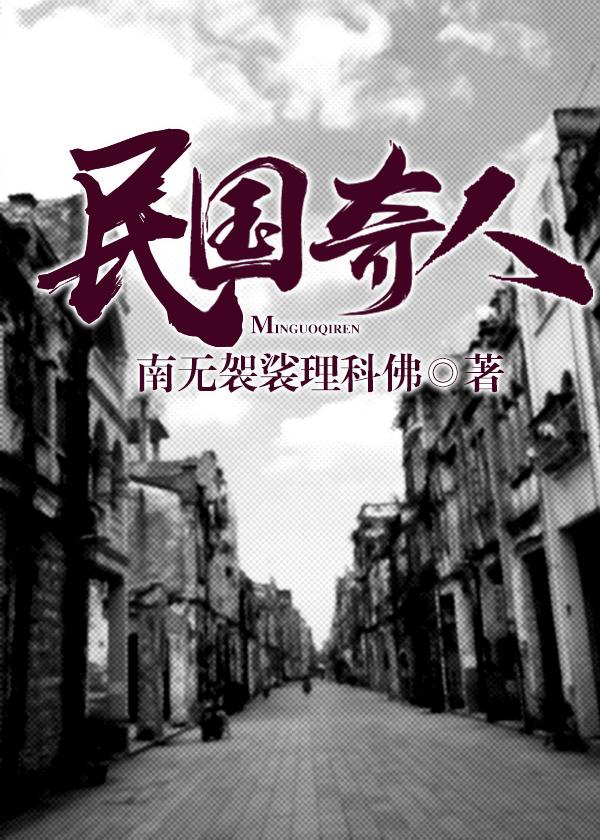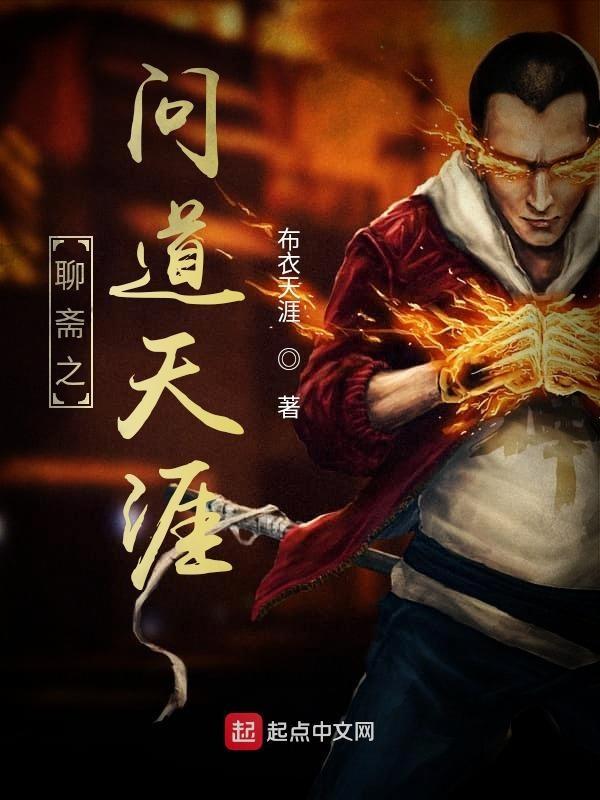鹅绒锁>坐看仙倾 > 第402章 埋在院中的铁箱(第1页)
第402章 埋在院中的铁箱(第1页)
雪水交加的雨丝穿过黎明时分的天光,像是无数银色细线,疏疏地洒满天空。
永安大街的左右两侧,琉璃瓦顶之上全都积起了一层冰水,而后在北来的寒风吹拂之下结成一片冻霜。
彼时,来自南北仙宗的使团正。。。
雨自南方来,初时细密如针,继而倾盆如注。山洪咆哮着撕裂山谷,泥石流裹挟着断木残瓦奔涌而下,将小村与外界彻底隔绝。那夜,天地失序,人声湮灭于雷鸣之中。可就在最深的黑暗里,一盏灯亮了。
不是火把,也不是符?之光,而是从老药农手中升起的一豆微明??他用油布护住半截蜡烛,稳稳举过头顶,照亮众人惊恐的脸庞。他声音沙哑却沉稳:“别慌,还有路。”
这人便是季忧的化身所化,十年行医于荒野,足迹遍布南疆瘴地、北漠孤镇、东海渔村。他不自称仙,也不受供奉,只在病榻前熬药,在灾荒中分粮,在孩童高烧不退的深夜守至天明。人们不知其名,只唤他“柳先生”。
此刻,他正蹲在断桥边查看水流。雨水顺着草帽边缘成串滑落,打湿了粗布衣襟。身后村民围作一圈,眼神里满是依赖与敬畏。有人低声说:“一定是观微里的神仙派他来的。”另一人摇头:“神仙哪会穿这么破的鞋?分明是菩萨转世。”
季忧没听见这些话。他的心神全系在河面上那一道若隐若现的藤蔓浮桥上。这是他临时教大家编的,用百年山藤与麻绳绞合,两端系在两岸巨石之上。虽简陋,却是唯一的生路。
“先送孩子和老人过去,”他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泥,“一个接一个,抓牢绳索,不要回头。”
风仍在呼啸,但人群已不再混乱。一位母亲抱着婴儿率先踏上浮桥,每走一步,木板便剧烈晃动,仿佛随时会被洪水吞噬。可当她走到中途,忽然听见岸边传来笛声。
清越,低回,像春溪绕石,又似晚风拂林。
是柳笛。
那旋律不成调,却奇异地安抚人心。村民们抬头望去,只见老药农坐在一块高岩上,唇间轻含柳笛,双目微闭,仿佛不是在吹奏,而是在倾听某种只有他能听见的回应。笛音一起,连狂风都似缓了一瞬。
终于,第一批人安全抵达对岸。欢呼尚未出口,一声巨响自上游炸开??一座拦水坝崩塌,浑浊巨浪如黄龙扑来!
“快撤!”有人嘶吼。
浮桥剧烈摇晃,几近断裂。几个尚在桥上的村民惊叫着跪倒,眼看就要被卷入激流。
就在这刹那,季忧跃起,身形竟快得不像凡人。他冲至桥头,双手猛然按地,口中低诵《太初正典》第六卷“承重之章”中的心法:“身如砥柱,意若江海;我不退时,万涛亦止。”
刹那间,一道青气自他脚底蔓延而出,迅速凝成九根虚影石桩,深深扎入河床。浮桥顿稳,宛如有了根基。村民趁机爬完最后一段,全部脱险。
待最后一人登岸,季忧才缓缓收回灵力。他脸色苍白,嘴角渗出一丝血迹??这一式耗损极重,非大德不可轻用。但他只是抹去血痕,默默收起柳笛,转身走向村子废墟。
救援官府终于赶到,带着舟船与器械。带队的是位年轻巡防使,正是十年前观微书院第一批学子之一。他一眼认出那人背影,急忙追上:“前辈!您……您是当年救蜀山瘟疫的那位‘无名医者’?”
季忧未答,只问:“粮食到了吗?”
“到了,三车米粮,两箱药材。”青年急切道,“我们连夜赶来的。可您怎么总出现在最难的地方?上次苗岭雪崩,前年阴山旱灾……是不是您一直在暗中指引我们?”
季忧终于回头,目光温和如旧日槐树下的春风。“我没有指引任何人,”他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而你们,正在成为别人眼中的光。”
青年怔住,久久不能语。
翌日清晨,雨停云散。阳光洒在泥泞的大地上,映出无数晶莹水珠。村民们自发清理废墟,重建家园。有孩子捡到一支断裂的柳笛残片,捧给族长看。老人接过,轻轻摩挲,忽觉指尖发热,那断笛竟泛起淡淡青光,旋即消散。
当晚,全村设宴答谢恩人。席间酒肉飘香,笑语喧哗。可当人们四处寻找柳先生时,却发现他早已离去,只留下一封信,压在灶台上的陶碗之下。
信上写道:
>“诸位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