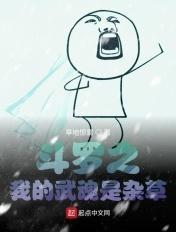鹅绒锁>农家子,但人上人(科举) > 第209章(第1页)
第209章(第1页)
这样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行径,在河东路学问大家许中恺到来之后,并且由王景禹明确了他将作为出使的一员,共同前往北齐之时,更是达到了顶峰。
两国边境争锋不得不进行的谈判,带上这样一个学问家能有什么用!?
又过半月,双方的出使和谈判日程最终敲定。
走完了两路边线的王景禹,整个团队也全部聚齐,由暂时被北齐均码占领的麻谷寨为入口,入北齐,往北齐西京进发。
在他们的出使团,初入麻谷寨时,麻谷寨的大景寨民以及被俘以后在齐军的看守下修筑寨中城防的大景军兵士,在北齐军兵的默许下,自发的来到了王景禹使团所必经的道路两旁。
车马潇潇,车帘滚动,由北齐官兵负责开路。
两排北齐士兵严密守卫的身后,是沉默又拥挤的大景军民。他们目光复杂的看着大景朝的高官,在麻谷寨被占将近两个月之后,第一次出现在这座大景朝的城寨之内。
看着紧闭的车帘,即将由此经过,驶往北齐西京,执行所谓的谈判和交涉。
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前途和命运?
他们这些蝼蚁一般的百姓与低级兵士,在两国的谈判桌上,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存在?是不是连筹码都算不上?假若此时车帘之内这位大景两路安抚使,真的能不把他们忘记,那他们从今往后,究竟是会就此成为北齐治下之汉民百姓?抑或成为北齐任意处置的战俘奴隶?还是会被不忘记他们的大景朝带回代州或者真定府诸地安置?
无论哪一种选择,都将深刻的改变他们的个人和家庭命运。
然而,这种命运完全不由普通人自己掌控,他们要处在这种对未来的担忧和不确定之中,可以做的只有——等待。
等待命运的最终宣判到来。
所以,当他们面对着自己大景朝的主事大官,自面前驶过之时,没有任何激动的表达。
他们只是关心关切的注视,但是无言沉默。
突然,车帘翻动之中,一位紫衣锦带乌帽黑靴的官员走了出来,立于马车前侧。
这一身品级分明的官服,使人们立刻得以知晓他的身份。待人们看清了这位官员之时,却发现,这位大景朝的两路安抚使,两国所言传的边事主事之人,竟然如此年轻!
原本的压抑和静寂被打破,人群之中开始了窃窃私语。
王景禹在越发好奇的百姓议论声中,只恭谨向两侧的大景朝军民拱手躬身,之后什么都没说,就同样这般默默的站立在车头之上,迎着五月的热风,直至朔州刺史迎送,马车出寨。
这一场官民之间,无言的注目和迎送。
却让今日身临其境的麻谷寨军民,感慨万千。矗立街头的百姓们久久没有散去,萦绕在无数人心间的,是一个疑问。
为什么这位大景朝的两路安抚使,明明什么都没有说,明明一句成承诺都未曾名言……
可这心里,却无端的燃起了几点希望灯火?
人们互相注视之后,隐隐达成了一种共识。
好像,这个主两国边事的大官,会重视他们这些普通的百姓?不会将他们视为连筹码都算不上,可以抛诸脑后丶随意被弃置的蝼蚁?
第174章
与大景朝南北相对的北齐国,占据了北方广阔的疆域,由于疆域过大交通不便,北齐一直以来施行的都是五京制,以及四时捺钵制度,北齐的皇帝会根据不同季节在五京或者其他地区进行巡视和狩猎,他们的政治中心并不会固定于某一京。
如今,齐国的皇帝,正在南京。
齐朝的南京,就位于后世现代的北京。
距离两国的边界县,距离不过百里。王景禹等人两日之后,就抵达了南京城外,由齐国的使臣出城迎接,当天即入住南京的对大景朝使馆。
齐国此次负责接待的接待官,正是北齐位于南京的南枢密
院枢密副使萧创。
两国此前邦交日久,自签署了和平协议之后,就互相之间制定了一套相当复杂,充分表示对各自尊重的礼仪体系。就连对于两国使臣的接待,也要单独与其他任何邦交国家区分开来,单独设置接待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