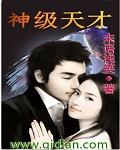鹅绒锁>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 第126章 Lascia chio pianga(第7页)
第126章 Lascia chio pianga(第7页)
哪怕是一首短小的咏叹调,也可能承载一个时代的回声。
李锐低声道:“所以听这些作品,其实是在听他们的世界。
“对。”江临舟点头。
“每个时代的音乐,都是那个时代的语言。
巴洛克讲秩序,古典讲理性,浪漫讲情感。
哪怕没有文字,你也能听出那个时代的人在思考什么。”
他抬起目光,望着舞台。
灯光再次调暗,新的乐手正准备入场。
“我们现在听韩德尔,不是为了模仿十八世纪的人。
而是为了在今天,去理解当年他们在追寻什么。
音乐从来不只是被演奏的,而是被传递的。”
李锐靠在椅背上,沉默片刻,轻声笑道:
“听你这么说,突然觉得音乐好像也有记忆。”
江临舟也笑。
“有啊。它记得每一个人曾经感受过的东西,
哪怕过了几百年,只要你听见,它就会被唤醒。”
灯光重新亮起,
舞台上的乐手起身鞠躬,掌声持续了好一阵。
当幕布缓缓合上,灯光再次转为柔和,
意味着这一场演出彻底结束。
片刻的静默之后,工作人员开始移动谱架和椅子,
后台传来轻微的脚步与低语。
新的节目单正被换上,
礼堂的空气里弥漫着那种过渡的气息
一场结束,另一场即将开始。
江临舟望着舞台那道被灯光切开的缝隙,
忽然有种难以言说的感觉。
他不知道是因为那首咏叹调的余韵还未散去,
还是因为在这一刻,他似乎更清楚地意识到了什么。
每个人的音乐都不一样。
哪怕弹的是同一首曲子,
音色,气息、节奏的呼吸,都会带出那个演奏者自身的痕迹。
那不是技巧的差别,而是一种无法模仿的存在。
他想到比赛时遇到的那些人
周明远、陈雨薇、赵一鸣。
他们的音乐各自独立,
像在同一个世界里却讲着不同的语言。
而那语言的差异,正是他们的灵魂在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