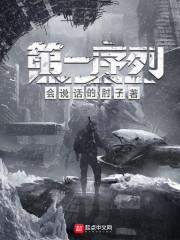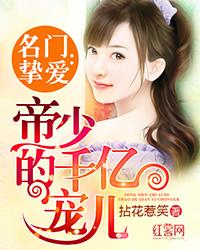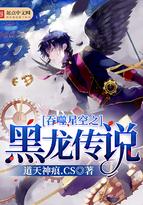鹅绒锁>状元郎 > 第二百七十章 大宗师震怒(第1页)
第二百七十章 大宗师震怒(第1页)
“谁不去谁是孙子!”先生们便一起跟着海教谕,浩浩荡荡来到了县衙大门前。
守门的衙役看到这么多读书人气势汹汹而来,赶紧一面禀报进去,一面阻拦道:“县衙重地不可擅闯,有事递状子!”
“你们先在。。。
苏录怔立原地,耳中嗡鸣不止。那伙计的话如重锤砸在心口,震得他四肢发凉。母亲病重?怎会如此突然!前月家书还说她身子渐好,夜里纺纱虽久,却不咳喘了。怎不过一月光景,便到了“盼归”之地?
他弯腰拾起李慎之的信,指尖微颤。信纸已皱,墨字模糊,仿佛预示着某种不可挽回的裂痕。去京赴考时,母亲送至村口,握着他手说:“儿啊,莫挂念我,功名要紧。”那时她尚能行走,还能笑着挥手。如今……他不敢想下去。
“来人呢?”苏录强自镇定。
“在后院歇着,是个老仆,说是您舅父派来的,一路快马加鞭,昨夜到的城外,今晨才进城。”
苏录点头,转身回屋,匆匆收拾包袱。笔墨、札记、《屯田疏》抄本尽数包入,又取出几两碎银塞进袖中。他不能久留,但也不能仓皇离去。此番返乡,若母亲真有不测,守孝三年,会试便要推迟;可若不去,为人子者何以立足天地?
陈文昭闻讯赶来,见他神色黯然,已知大事不好。“你要走?”
“非走不可。”苏录声音低沉,“母命危矣,岂敢耽搁?”
陈文昭沉默片刻,忽道:“那你得快去快回。明年春闱,万不可误期。”
“我知道。”苏录苦笑,“可生死由天,行程哪能预料?”
“不如这样??”陈文昭从怀中取出一封荐书,“这是我叔父写给扬州知府的信,你路过扬州时可投递,或能借驿马疾行,省下四五日脚程。”
苏录感激接过:“大恩不言谢。”
当夜,他焚香祭拜祖宗牌位,写下辞别帖呈于杨廷和府门,并托李慎之代为致意。次日清晨,天色未明,苏录便牵马出城。北风凛冽,吹动枯枝如鬼爪摇曳。他回首望了一眼京城巍峨城楼,心中百味杂陈:这曾是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中心,如今却不得不暂别。而这一别,或许便是命运转折之始。
一路上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过了徐州,进入南直隶地界,村庄渐显凋敝。田亩荒芜,沟渠堵塞,偶见农夫扶锄叹息。苏录停下询问,方知去年秋赋未减,地方官吏仍按旧额催征,百姓无力承担,只得弃田逃亡。他默默记下所见,心中悲愤难抑:朝廷诏令减免江南赋税三成,为何下情不通?政令不出宫门乎?
行至扬州,依陈文昭之计投书知府。那知府姓徐,乃先帝旧臣,素重文士,读罢荐书当即召见。听闻苏录是乡试第五名经魁,且撰有《屯田疏》,更是刮目相看。当即拨驿马一匹、随从两名,准其借道疾驰。
自此一日百余里,马不停蹄。越近凤阳,心越焦灼。第三日傍晚抵达家乡小镇,只见村口柳树下跪着一名老仆,正是舅父家中长随。见苏录下马,老仆嚎啕大哭:“公子……夫人已于三日前仙逝!临终前只念您姓名,不肯闭眼……”
苏录脑中轰然炸裂,双腿一软,几乎跪倒。他踉跄奔入家门,推开柴扉,院中白幡高悬,灵堂设于堂屋。棺木漆黑,香烛缭绕,母亲遗像挂在正中??那张熟悉的面容,此刻竟显得如此遥远。
他扑跪在地,抱住棺木放声痛哭:“娘!儿子回来了……儿子不孝,未能见您最后一面……”
泪如泉涌,滴落在冰冷的棺盖上。屋内无人劝慰,唯有烛火摇曳,映照着他颤抖的身影。舅父悄悄进来,轻抚其背:“孩子,节哀。你娘走得很安详,只是等你不至,最后喃喃一句‘吾儿必成大器’,便咽了气。”
苏录伏地不起,整夜守灵。翌日清晨,族中长辈主持丧礼,邻里纷纷前来吊唁。有人赞他光宗耀祖,也有人暗叹“举人又如何?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这些话他都听见了,却不辩解。他知道,功名再高,若不能护亲周全,终究是空谈。
七日斋醮过后,苏录亲自执锹bury母亲于祖坟之侧。坟前立碑,亲书“显妣苏母张氏之墓”,落款“孝男苏录泣立”。碑石未干,雨便落了下来,混着泪水滑过脸颊。
此后他闭门不出,在母亲房中整理遗物。翻箱倒柜间,发现一只旧木匣,锁已锈蚀。撬开一看,竟是十余年来他寄回家的每一封信,皆被母亲用红绳仔细捆扎,压在枕下。最上面一封,是他中举后写的报喜信,边上还贴着一张黄纸??那是她请人抄录的乡试榜文复印件,字迹歪斜,却一笔不落。
苏录捧信良久,终于明白:母亲从未识字,却把他的每一次消息,当作性命般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