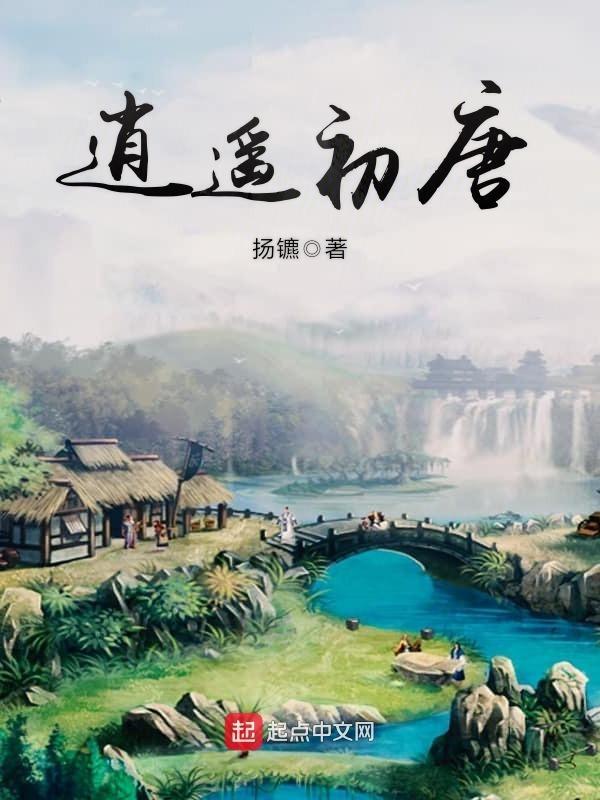鹅绒锁>状元郎 > 第二百六十九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第1页)
第二百六十九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第1页)
一家人狂喜了好半天,才想起来问问另外两个过了没。
“都过了!”尤幕友笑道:“而且苏满还高居第三,也非常优秀啊!中秀才已经十拿九稳了。这回你们老苏家八成要双喜临门,三阳开泰都有可能!”
“是。。。
苏录站在贡院门口,风从檐角掠过,吹得他衣袍猎猎作响。天还未亮,青灰色的云层压在头顶,像是砚台里未化开的墨。他抬头看了一眼那块写着“贡院”二字的匾额,笔力遒劲,是先帝御笔亲题。此刻,千百士子已列队而立,手持考牌,静候入场。
他深吸一口气,将包袱紧了紧。里面除了笔墨纸砚,还有一件母亲亲手缝制的夹袄??虽已是春末,可夜里仍寒,她总怕儿子受凉。苏录没舍得穿,只带在身边,权当是个念想。
“苏兄。”身后传来一声轻唤。他回头,见是同乡举子陈文昭,面上带着几分疲惫,却掩不住眼中的热切。
“你也来了。”苏录微笑颔首。
“今科必中!”陈文昭握拳低语,“我昨夜梦见文昌星落于案前,笔生莲花,墨涌江河!”
苏录笑而不答。他知道这不过是士子们临考前的自我鼓劲罢了。梦兆如何,终究不如真才实学来得踏实。但他并未泼冷水,只道:“但愿你我皆得如意。”
二人随队缓步前行,穿过三重大门,经搜检官逐一查验。有人大呼冤枉,因袖中藏了一块姜片驱寒被误认为作弊;有人默然退场,只因砚台底下刻着前人佳句,被视为夹带。场面喧闹又肃穆,像一场庄严的献祭。
终于轮到苏录。搜检官翻看他包袱,目光落在那件夹袄上,顿了顿,问:“此物何用?”
“御寒。”苏录平静答道。
那人点点头,放行。
入号舍后,天光初现。苏录坐在狭小的空间内,铺纸研墨,四壁斑驳,墙角蛛网轻摇。隔壁传来咳嗽声,再远些,则是??翻书页的动静。他知道,这一刻,全天下最聪明的一批人都在这方寸之间,与文字搏斗,与命运角力。
辰时整,提调官高声宣读题目:
“子曰:‘君子不器。’试论之。”
苏录闭目片刻,脑海中如潮水般涌起诸家注解。程子言“君子不可拘于一艺”,朱子谓“志于道者不当如器具之各限其用”。然此题看似平易,实则极难出彩。若循规蹈矩,不过中上之文;若剑走偏锋,又恐触怒考官。
他睁开眼,提笔蘸墨,在纸上写下破题一句:
**“君子以身为天下用,而非为一身之用。”**
笔锋一落,心中豁然开朗。
接下来,他不再纠缠于字句训诂,而是直指本心??何为“器”?器者,有定形、有限用、有所待而成者也。锅碗瓢盆,各有其职,然终不能互换。而君子不然,可为政、可讲学、可临阵、可退隐,随势而化,应机而动,岂能以一技一艺囿之?
文中更引周公吐哺、诸葛躬耕、范文正断齑画粥等事,说明圣贤之所以超然于众,正在于其不执一端,心怀天下。最后结语云:
**“故君子非不用器,乃不滞于器;非不精于艺,乃不止于艺。其身如江海,纳百川而不自满;其志如日月,照四方而不私光。此所谓大用无方,大道无形。”**
写罢通篇,苏录搁笔,额上微汗。他知道,这一篇未必能夺魁,但至少,是他心中所信。
三日考毕,苏录步出贡院,双腿几乎麻木。京城街头已恢复喧嚣,酒楼茶肆传出丝竹之声,仿佛无人记得这几日有多少人曾在号舍中呕心沥血。他回到客栈,倒头便睡,直至次日下午才醒。
醒来时,桌上摆着一碗尚温的鸡汤面,旁边留条:“苏兄若饿,请自取食。陈文昭留。”
他心头一暖,吃了面,正欲出门致谢,忽听街上传来锣鼓声。一队差役敲锣开道,中间一人骑马披红,手持捷报,高声唱道:
“捷报贵府老爷苏录高中顺天府乡试第五名经魁!”
苏录怔住。
门外人群涌动,贺客纷至沓来。客栈掌柜亲自捧出红绸挂门前,邻舍妇人端来糖糕果子,连昨日嫌他吵闹的老翁也拄拐前来道喜。
他站在屋檐下,看着那张黄纸黑字的榜文复印件,一时竟不知悲喜。
第五名,已是极佳成绩。但他清楚,这只是开始。真正的战场,还在三年后的会试、殿试。
当晚,陈文昭设宴相庆。席间觥筹交错,众人劝酒不休。一位老秀才拍着他肩头叹道:“我考了六次,鬓发尽白,终无所成。你年方二十有二,便已登科,真是天佑英才啊!”
苏录举杯欲饮,手却微微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