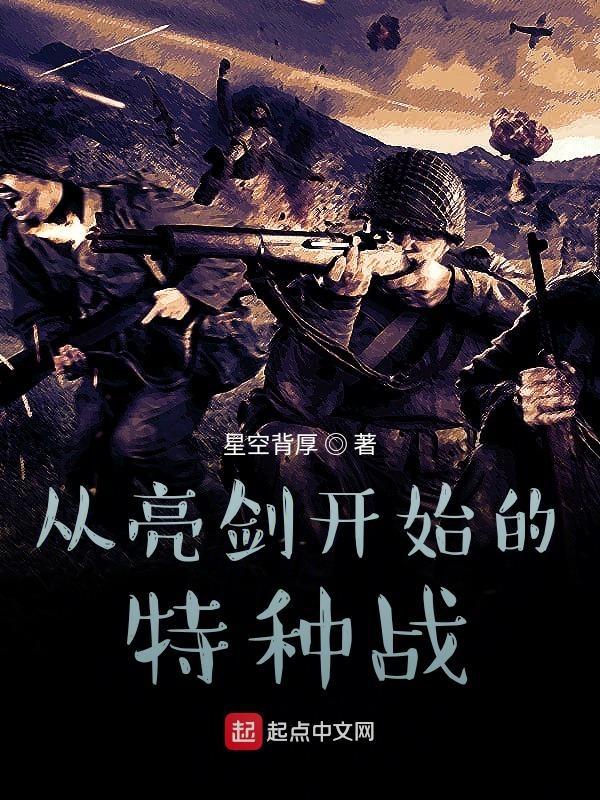鹅绒锁>小巷原来那么长 > 4550(第2页)
4550(第2页)
在我去世的时候,你不哭。
在我葬礼的时候,你不哭。
在我去世三年以后,在我给你买的压缩饼干都过了保质期的时候,你却莫名其妙的哭了。
到底搞什么啊陶天然?
陶天然低低的说:“放手。”
程巷紧紧攥着她细瘦的手腕。
陶天然用力一挣,程巷的指间便空了。陶天然风衣下摆撩动的匆匆往前走去,很快消失在了胡同转角。
程巷垂头站在原地,良久,将右手抬起来,很用力的反反复复擦拭着虎口。
方才陶天然的眼泪打落在这里。
原来那么冷的人,眼泪也是烫的。
一位大妈骑着自行车路过她身边:“姑娘,站着发什么呆呢?你这糖油饼怎么拿袋子装啊,再闷一闷可就不好吃了。”
程巷抬眸,一声“刘大妈”哽在喉头。
哦,不能叫。
她早已不是程巷了,又怎么会认识在这胡同里住了一辈子的邻居大妈呢?
于是她只是抬着眉眼笑笑:“谢谢您。”
拎着糖油饼往自家的四合院走去。
走到门口却又不敢敲门,就那样直挺挺站着,春日的阳光烫在她后颈,令她后脖根发紧。
恰好这时马主任走出来,一边扭回头抱怨程副主任:“没开没开,都跟你说了那家糖油饼摊还没开呢,非要我去看什么看……”
说话间,撞见了门外的程巷。
程巷勉强扬了扬唇:“那什么,我刚好在附近办事,以前听程巷说您二位爱吃这个,我便买了点带过来。”
马主任接了她递上的袋子。
她转身要走的时候,马主任叫住她:“哎,姑娘。”
程巷回眸。
“小巷她,”马主任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鼻尖,程巷这才发现自己的这些小动作,其实是跟马主任学的。马主任问:“她还跟你说过我们的什么?”
程巷笑了。
她站在越过四合院灰瓦屋檐打来的一束斜斜阳光里:“她说程副主任天天在家拖地,抱怨你的头发到处掉,你就很得意的说掉了这么多,你的头发还是浓。”
“她说每次你感冒,程副主任都会瞒着大夫,悄悄给你买一个冰淇淋,说这样能降体温,说他从小就这么吃。”
“她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每次出门去胡同里遛弯儿,还是手牵着手。”
马主任摇摇头:“现在不牵啦。”
程巷看着她。
“我们的女儿,她连个相伴一生的人都没找着就没了。我们不能牵啦,她看了,多受刺激啊。”马主任说着,扬了扬手里的糖油饼:“姑娘,你吃早饭了么?没吃的话,我打了豆浆,一起吃点?”
程巷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很用力的点头,跟八辈子没吃过饭一样。
马主任在四合院里支一张小圆桌,拿大瓷盘装了程巷带过来的糖油饼,自己打的豆浆则装在一个搪瓷大碗里,淡黄色,有很复古的国民水墨印花,谁要喝,就自己拿小瓷碗盛一碗,加多少糖全凭自愿。
马主任血糖高,她不加糖。
四合院地板上铺着小块的方砖,磨损已很严重了。四周种着槐树、枣树,还有程巷卧室里的梧桐树露出头来。其实气味没那么好闻,因为邻居大爷养的鸽子把随处都当厕所。
暖气从屋里熏出来,三人坐在屋檐下,感受着早春的阳光。
程巷没想过还有这样的机会。
跟父母坐在一起,吃一顿简简单单的早饭。
她躺在漫天飞雪的斑马线上时,除了陶天然,想的就是这爸妈喜欢的糖油饼。因为她冷,特别冷,人一冷胃里就空,总要想一些扎实的、温暖的、能填饱自己的心和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