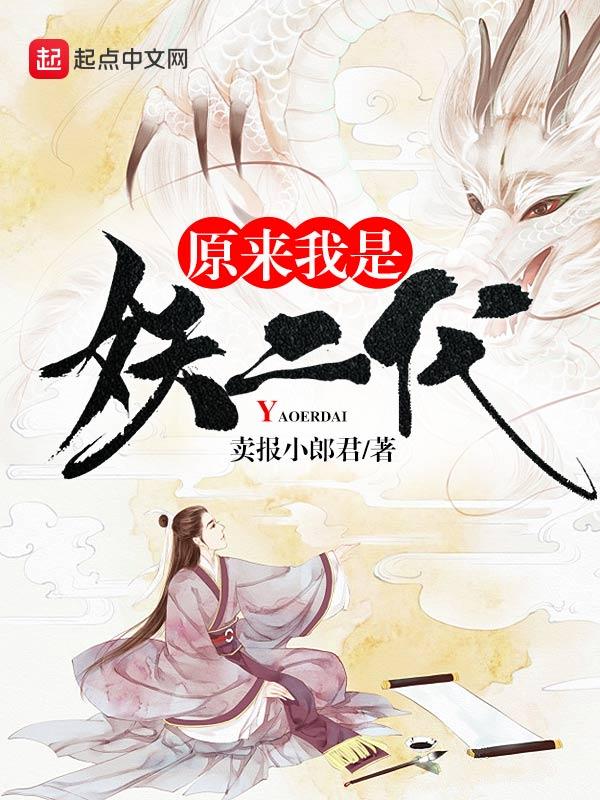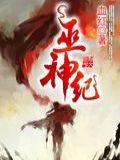鹅绒锁>没钱怎么当明星 > 第二百四十三章 怎么感觉处处是商机啊(第3页)
第二百四十三章 怎么感觉处处是商机啊(第3页)
机场安检口,八位侗族老人穿着统一的深蓝布衣,银饰叮当作响。过安检时,金属探测器报警,工作人员愣了一下,随即看到她们身上层层叠叠的古老银饰,神情从疑惑变为敬意。
一位年轻空乘主动蹲下帮吴阿婆调整肩带,轻声问:“奶奶,你们是要去唱歌吗?”
老人点点头,用侗语说了句什么,孙女翻译道:“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所以一定要唱给全世界听。”
航班起飞那一刻,林小树望着舷窗外翻涌的云海,忽然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次出行,而是一场漫长的归途。
十个小时后,纽约肯尼迪机场外,数百名华人华侨举着横幅迎接:“欢迎中国声音!”“致敬平凡的伟大!”
当地主流媒体也纷纷到场拍摄。CNN记者拦住林小树提问:“你认为这场演出,能在西方引发共鸣吗?”
他想了想,说:“你们习惯听英雄的故事,但我们带来的,是幸存者的故事。他们没有超能力,没有巨额财富,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活成了光。我相信,这种光,任何文化都能识别。”
次日,联合国总部大厅内,布置成一座融合东方意境与现代科技的展厅。“普通人之声”全球巡展正式开幕,入口处矗立着一块巨幅屏幕,滚动播放《我在》系列精选片段。
各国代表陆续入场,有人皱眉,有人好奇,也有人不屑一顾。
直到灯光暗下,侗族大歌响起。
那一刻,全场静默。
八位老人身着盛装,缓步走上中央舞台。没有伴奏,没有扩音,仅凭人声构建出恢弘的和声空间。古老的音律如风穿林,如水漫石,穿越语言与种族的壁垒,直抵人心。
一曲终了,足足十秒钟无人鼓掌??所有人都沉浸在余韵之中。
然后,掌声爆发,经久不息。
许多外交官眼含热泪,日本代表起身鞠躬,法国文化参赞当场写下笔记:“这才是人类共通的情感语言。”
林小树走上台,接过话筒。
他没有讲宏大叙事,没有提政治理念,只是讲述了三个故事:
一个是张小勇在塔吊上读诗的样子;
一个是李春梅在侗寨挨家挨户采集歌声的三个月;
最后一个,是他父亲念诗那晚,他跪下的原因。
“我不是在请求原谅。”他说,“我是终于明白,有些爱,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太忙,忘了回头看看。”
台下寂静无声。
他说完,全场起立鼓掌,持续七分钟。
事后,《纽约时报》评价:“这不是一场演出,而是一次灵魂的对话。它提醒我们,在算法与资本之外,人类仍保有最原始也最珍贵的能力??用声音传递尊严。”
回国当天,林小树没有回家,而是直奔医院。
黄振国突发脑梗,虽抢救及时,但右半身暂时无法活动。他在病房里仍戴着助听器,反复听《我在》第一集的音频版。
见到林小树,老人努力抬起左手,指了指床头柜上的《新概念英语》。
“还想学?”林小树笑着问。
老人艰难地点头,嘴里发出模糊的音节。
林小树坐下,翻开书页,轻声读:“LessonOne…MynameisJohn…”
一个字一个字,带着耐心,如同当年父亲教他认字那样。
窗外,春阳正好,照在两代人的肩头。
他知道,这条路还很长。
但他也清楚,只要还有人愿意开口,就永远会有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