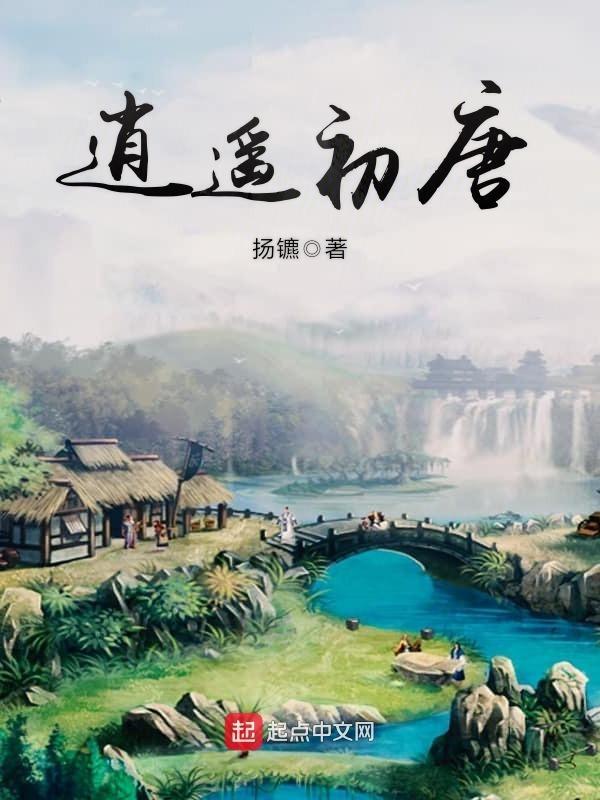鹅绒锁>七零易孕娇娇女,馋哭绝嗣京少 > 第580章不行就离婚吧(第2页)
第580章不行就离婚吧(第2页)
第一天晚上,录音机里传来一个颤抖的声音:“我十二岁就被许配给了四十岁的男人……我不想嫁,可我不敢说……我怕家里断粮……”
整个营地陷入沉默。卓玛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第二天清晨,她召集所有成年女性开会。没有宣讲,没有指责,只是放了几段录音??来自越南、缅甸、印度的女孩讲述童婚、性剥削、身体羞辱的经历。
“这不是你们独有的苦难。”她说,“这是千万个女孩正在经历的事。但我们能改。”
她拿出一份《女童保护公约》草案,逐条解释:禁止早婚、保障入学权、设立紧急庇护机制。“我们需要你们签字。不是为了对抗谁,而是为了守护我们的女儿。”
起初无人回应。直到那位曾因女儿例假被赶出帐篷而痛哭的母亲站了起来,将手掌按在纸上:“我签。哪怕明天就被赶出村子,我也要签。”
第二个、第三个……最终,二十三位母亲和七位祖母签下了名字。村长的儿子怒吼着冲进来,却被自己的母亲拦住:“你要是敢动她们一根手指,我就烧了你的经书。”
那一刻,卓玛忽然明白:真正的变革,从来不是外来者强行推动的,而是当沉默的大多数终于开口时,风暴自然来临。
一周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处派员考察。他们带来了摄像机、评估表和一笔专项资金。负责人是个五十岁的德国女人,名叫安娜,戴着眼镜,说话温和但坚定。
“我们跟踪你们的项目已经两个月。”她在篝火旁说,“你们做的不只是教育,是在重建一种文化认知。这在全球高原地区都是首创。”
“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卓玛轻声答。
“可大多数人选择视而不见。”安娜凝视着她,“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明年三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全球边缘女性教育峰会’。你们需要一个舞台,让更多人看见这里发生的一切。”
会议结束后,卓玛独自走到山坡上。夜空清澈,银河横贯天际。她打开手机,江倩倩刚发来消息:
>“林小雨的网店上线了。第一单卖出去的是她妈妈绣的蝴蝶香包,买家留言说:‘这是我见过最有力量的手艺。’
>
>她昨天直播两小时,说了三次‘谢谢你们愿意听我说话’。
>
>卓玛,我们在救人,也在救过去的自己。”
卓玛眼眶发热。她抬头望星,仿佛能看到千里之外那个瘦弱身影坐在镜头前,指尖抚过绣线,一字一句讲述苗族神话里的创世故事。
又过了十天,一场暴风雪突袭措玛村。风势猛烈,帐篷摇晃,电线断裂,唯一的发电机也被积雪压坏。夜晚降临,整个营地陷入黑暗。
但孩子们没有哭闹。她们围坐在教室里,借着手电筒微光,轮流朗读《女孩报》上的文章。央金带头唱起那首《我不怕黑》,其他人跟着哼唱。歌声穿透风雪,竟让人心生暖意。
凌晨三点,李岩带着两个牧民青年爬上山脊抢修线路。零下二十度,金属零件粘手即冻伤。他一边呵气暖手,一边调试电路,终于在黎明前恢复供电。
灯光亮起那一刻,全屋欢呼。达瓦央宗抓起相机拍下这一幕:十几个小女孩举着蜡烛,映照着黑板上刚写下的句子??
“只要灯还亮着,我们就不会迷路。”
春天悄然逼近。冰雪融化,溪流重新奔涌。村外草场冒出绿意,牦牛群开始迁徙。而“种子教师计划”也正式启动。两名本地妇女完成培训,成为首批本土女教师。她们的名字被刻在学堂门前的木牌上:白玛曲珍,四十二岁,文盲母亲,如今能读写三百藏文字;扎西拉姆,三十八岁,曾因难产失去两胎,现在每天教拼音和基础卫生常识。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用。”白玛曲珍对卓玛说,“以前我觉得女人就是生孩子、挤奶、烧火。现在我知道,我能教别人认字,这就是功德。”
卓玛握住她的手:“你不止有功德,你有尊严。”
与此同时,怒江园区内,“匿名开店”项目迎来首批海外订单。除了林小雨的“蝴蝶妈妈手艺”,还有三位归国女性分别上线了侗族织锦、傣族陶艺和羌绣产品。江倩倩亲自设计包装,每件商品附赠一张手写卡片:“这件作品背后,是一个重生的故事。感谢你,让她被看见。”
订单如雪片般飞来。纽约、伦敦、东京的买家留言:“请告诉创作者,她的勇敢打动了我。”“我愿为这份美支付双倍价格。”“这是我送女儿最好的成长礼物。”
江倩倩把每一条反馈打印出来,贴在心理辅导室的墙上。她希望每一个走进这里的女孩都能看到:这个世界,并非只有伤害。
四月中旬,克钦邦难民营传来喜讯:姊妹学堂已有五十六名女孩入学,其中三人已能用中文简单对话。她们用竹片做黑板,拿炭条当粉笔,在雨季漏水中坚持上课。视频连线那天,一个小女孩怯生生地说:“卓玛老师,我们也能考上大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