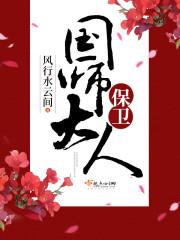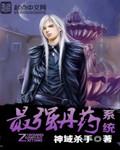鹅绒锁>耽美文女配系统让我做万人迷 > 30321 12喜欢(第1页)
30321 12喜欢(第1页)
夜色渐深,沈知意合上日记本,指尖在封面上轻轻摩挲。露台的风依旧温柔,却比白日多了几分凉意。她起身进屋,顺手打开书房角落的老式收音机??那是诸葛长薄亲手改装的信号接收器,能捕捉到全球范围内一些未加密的短波通讯。他总说:“真正的声音,往往藏在杂音里。”
电流滋滋作响,断续传来几段模糊对话:某地抗议集会的呼喊、偏远村落教师朗读课文的声音、还有某个电台主持人低沉地说着:“……今天我们收到一条特别留言:‘我终于敢对上司说“不”了,虽然明天可能就被辞退,但我第一次觉得呼吸顺畅。’谢谢你,沈知意。”
她怔了一下,随即笑了。
刚想关掉收音机,一段异常清晰的信号突然切入,带着某种熟悉的节奏感,像是经过精密调频。一个少年的声音响起,语速急促,背景有风声和脚步声:
>“我不知道这个频道有没有人听,但我在逃。他们说我‘情绪失常’,要把我送去矫正中心。可我只是不想再演那个乖巧懂事的儿子了!我读了你的书,你说‘真实不是错误’,那为什么我要被当成病人?”
停顿片刻,声音颤抖起来:
>“我现在躲在火车站的厕所隔间,手机快没电了。如果你们听见,请告诉我……我还能去哪里?”
沈知意的心猛地揪紧。她立刻打开电脑,调出信号溯源程序,却发现这段广播并未通过常规网络传输,而是借用了极少数仍在运行的模拟电台中继站??这种技术早已被淘汰,只有少数地下组织或偏远地区还在使用。
“回声计划”的自动监听系统同时发出警报:过去二十四小时内,类似匿名广播在全球出现了七次,分布在东欧、南美、东南亚。内容高度相似??都是青少年,在极端压抑的家庭或社会环境中觉醒,试图联系外界求助,却无法接入互联网,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发声。
她迅速起草一封加密邮件发给林晚:“有人正在自发复制我们的模式,用旧式电台传播‘反剧本’思想。这不是偶然,是连锁反应。”
回信很快抵达,只有短短一句:“非洲已有三个村庄的孩子开始自办‘自由电台’,用太阳能设备播放自己写的诗和故事。他们管自己叫‘夜莺分队’。”
沈知意闭上眼,鼻尖发酸。
原来火种真的烧起来了。
第二天清晨,她召集技术团队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将“回声计划”升级为**去中心化匿名网络**,让哪怕没有网络、没有电力的人,也能接收到信息,并安全传递自己的声音。
“我们可以重建一套基于短波+蓝牙Mesh的离线通信系统。”年轻的技术员小陈说,“U盘只是起点,真正要做的,是让每一份觉醒都成为中继站。”
“就像病毒一样扩散?”有人问。
“不。”沈知意摇头,“不是病毒,是免疫系统。我们不是在感染世界,而是在唤醒它原本就有的防御机制??质疑的能力。”
方案敲定后,她亲自参与编写第一批“种子包”内容。除了《情感识别手册》精简版、《我们不是剧本》音频节选,她还加入了一套名为《提问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全是看似简单的问题:
>“你是因为真心喜欢,还是因为怕被讨厌才答应?”
>“如果没人看着你,你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
>“你现在的痛苦,是在保护自己,还是在成全别人的期待?”
这些问题,曾是她在系统控制下最恐惧的东西。如今,它们成了武器。
一周后的深夜,第一批发射装置随一艘货轮秘密启航。这些装置伪装成气象监测设备,将在沿途十二个港口自动激活,向周边区域循环播送“回声计划”的接入方式。每个装置寿命有限,最多运行三个月,但足以点燃火苗。
沈知意站在码头目送船只远去,海风吹乱她的长发。身旁站着从非洲赶来的林晚,两人许久无言。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林晚忽然开口,“那些曾经投资‘万人迷系统’的财团,现在正大力推广一种新型AI伴侣服务,宣称能‘治愈孤独’。广告词写着:‘给你最懂你的爱’。”
沈知意冷笑:“又是旧剧本的新包装。”
“但他们没想到,”林晚望着漆黑海面,“越来越多用户开始反向训练AI??不是让它变得更顺从,而是故意输入矛盾指令,逼它崩溃。有人录下视频上传,标题叫《我和我的AI吵架的一百种方式》。”
她轻笑出声:“他们在练习说‘不’。”
“是啊。”林晚转头看她,“而且越来越多人发现,真正的亲密,不是对方永远理解你,而是你敢于暴露不被理解的部分。”
雨又下了起来,细密如针,落在海面无声消融。
回到住处,沈知意打开邮箱,发现一封来自“夜莺”的新消息。这次没有录音,只有一张照片:一群孩子围坐在篝火旁,手里举着纸牌,上面用不同语言写着同一句话:
>**“我们在说话,你能听见吗?”**
附言写道:
>“昨天,一个男孩当众撕掉了母亲为他安排的婚约请柬。他说:‘我不是来结婚的,我是来告诉大家,我不想活成你们想象中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