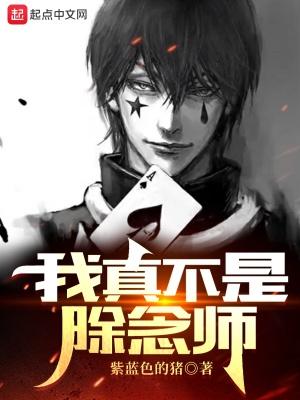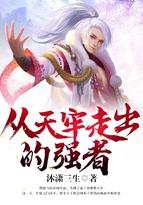鹅绒锁>傅律师,太太说她不回头了 > 第712章 好好珍惜和戚樾在一起的时光(第3页)
第712章 好好珍惜和戚樾在一起的时光(第3页)
这一晚,她守在ICU外,直到黎明破晓。
一周后,周晓雯脱离危险,转入心理科病房。她的父母第一次出现在探视室,老母亲抱着女儿嚎啕大哭:“妈错了,妈不该逼你快点好起来……你要是早告诉我们有多难受,我们就带你去看病啊!”
沈安宁站在门外,没有进去打扰。她知道,真正的疗愈已经开始??当家人终于学会倾听,而不是指责。
出院那天,周晓雯主动申请加入“倾听者训练营”。她在第一堂课上说:“我曾经用专业知识去安慰别人的家属,却从未允许自己软弱。现在我想学一件事:如何做一个会哭的母亲,也能成为一个好妈妈。”
掌声响起时,沈安宁悄悄退出教室。走廊尽头,戚樾抱着熟睡的途途等她。女儿的小脸上沾着饼干屑,嘴角还挂着梦中的笑意。
“她今天第一次自己站起来了。”戚樾低声说,“摇摇晃晃走了五步,然后扑进我怀里。”
沈安宁伸手抚摸途途的头发,忽然觉得腹中一阵轻微抽动。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她也在学走路呢。”
春天彻底来了。
“归途园”迎来新一轮改造。念安带着一群孩子在围墙内侧绘制巨幅壁画:左边是暴风雨中的小船,右边是穿过云层的阳光,中间是一条蜿蜒小路,路上有许多脚印,大小不一,方向一致。最前方的一双脚印,画得格外清晰,鞋底沾着泥,却坚定向前。
下方写着一行童稚的字:
>**“不怕走得慢,只怕停下不走。”**
与此同时,“归途之声”正式接入全国心理健康大数据平台,成为首个获政府认证的民间心理危机干预协作网络。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发来函件,肯定其在预防产后抑郁致极端事件中的突出贡献。
而沈安然在云南山村的教学日记也被整理出版,书名就叫《蓝雪花开了》。首印十万册全部售罄,所得收益全额捐入“归途计划”专项基金。
某日午后,沈安宁收到一封来自云南的信。信纸泛黄,边缘有些磨损,像是被反复折叠过许多次。打开一看,是沈安然的字迹:
>**姐姐:**
>今天有个小女孩问我:“老师,你为什么总是看着远方?”
>我说:“因为在那个方向,住着我最爱的人。”
>她想了想,跑回家拿来一幅画,送给我。画上是两个女人站在花园里,一个抱着孩子,一个仰头看天,天空飘着无数纸灯笼,每一盏都写着一句话。
>最近的一盏上写着:“妹妹,姐姐一直都在。”
>我哭了。
>原来光不仅能照亮别人,也能穿越千山万水,照回自己的心。
>我很好,勿念。
>等山花开满的时候,我会回来。
>到那时,我们一起种一片蓝雪花,好吗?
沈安宁读完,久久伫立窗前。
窗外,绣球花又开了一茬,粉的、蓝的、紫的,层层叠叠,如同永不褪色的承诺。途途在院子里追逐蝴蝶,笑声清脆如铃。戚樾坐在廊下修理一把旧摇椅,那是他特意从老宅搬来的,说将来可以放在花园里,供来访的妈妈们休憩。
沈安宁把手贴在隆起的腹部,感受着胎动一下下撞击掌心。她知道,另一个生命正在靠近这个世界,带着未知的伤痛与希望。
她轻声说:“我们会好好爱你的。”
就像当年那个雨夜里,如果有人对她说这句话,或许一切都会不同。
而现在,她终于成了那个能说出这句话的人。
风起了,吹动花园里的风铃,叮咚作响。新刻的陶罐在阳光下静静伫立,等待下一个名字的到来。
而在所有人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束光,正悄然渗进裂缝,温柔地,照亮了整片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