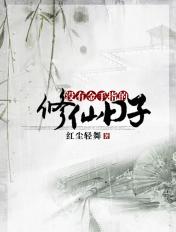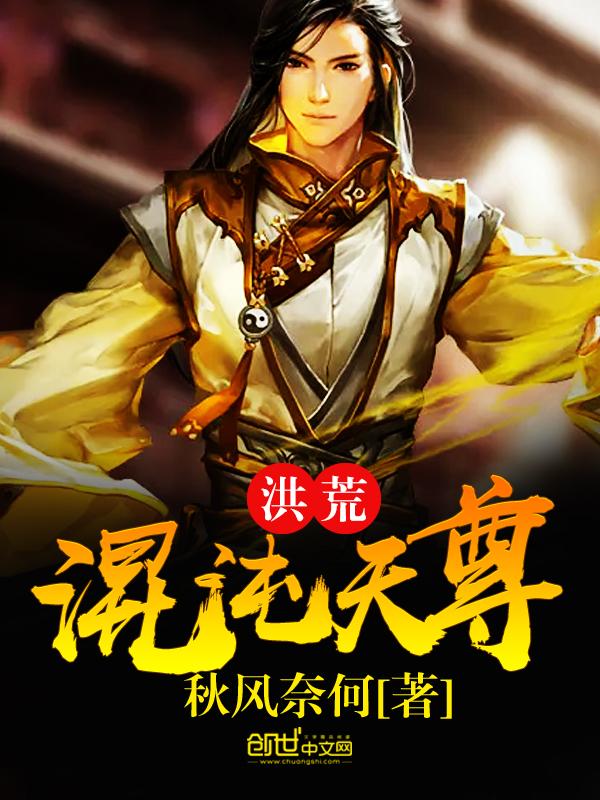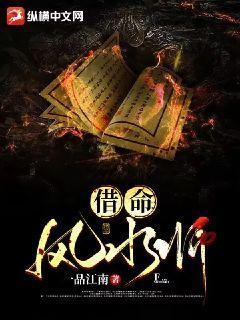鹅绒锁>1987我的年代 > 第675章 三粒扣子(第1页)
第675章 三粒扣子(第1页)
就在老两口在卧室话家常之际,外面楼道口传来细碎的脚步声。
夫妻俩互相瞧瞧,立马闭嘴。
没一会儿,外面的洗澡间门被推开了,隐约还传来说话声。
田润娥竖起耳朵听了许久,小声道:“是满。。。
五月的风穿过厂区老槐树的枝叶,簌簌作响。林小满站在车间门口,手里攥着那张“岗位之星”的红纸奖状,耳边还回荡着工友们的掌声。她低头看了看胸前别着的护士徽章??那是医院发的正式编制标志,银边白底,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和编号。阳光照在上面,折射出一道细碎的光,像一把小小的钥匙,打开了她心里某扇长久紧闭的门。
她把奖状折好塞进帆布包,转身走进更衣室。脱下蓝布衣裳,换上那件淡蓝色护士服时,手指微微发颤。这件衣服如今不再只是试岗时的奢望,而是她每一天都要穿上的责任。镜子里的女孩脸色依旧清瘦,眼底有淡淡的青痕,可眼神却比从前亮了许多,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点燃了。
下午三点,她骑车赶往医院。路上经过菜市场,特意拐进去买了半斤猪肝、一把菠菜??母亲最近血色素偏低,医生说要补铁。摊主是个胖婶子,见她来买,笑着问:“又给妈改善生活啊?你这闺女,真是没得说。”林小满腼腆一笑,付了钱,把菜小心放进车筐,用塑料袋盖好,生怕雨水打湿。
到了医院,正值交接班时间。呼吸科走廊里人来人往,家属提着热水瓶穿梭其间。她刚走到护士站,陈建国就迎上来:“小满,3床老爷子体温又升上来了,刚才量到39。2℃,主任让做物理降温,你去处理一下。”
“好。”她点头,迅速戴上口罩,洗手后推起治疗车就往病房走。
3床是位七十多岁的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姓赵,脾气倔,话少,但对林小满格外信任。前些日子高烧昏迷,还是她连续守了两个晚上,每隔半小时擦一次酒精浴,才稳住病情。老爷子醒来第一句话就是:“这丫头,比我亲闺女还上心。”
此刻老人躺在病床上,满脸通红,呼吸急促。林小满一边调低空调温度,一边解开他上衣扣子,用温水浸湿毛巾,轻轻擦拭腋下、颈部、腹股沟。“赵伯,您忍一忍,一会儿就好了。”她低声安慰,“等体温下来,我给您读报纸。”
老人哼了一声:“你念的那个《参考消息》,尽是外国事,听不懂。”
“那我讲点家常的?”她笑,“今早我弟打电话来说,他这次月考数学全班第二,语文也进了前十。他还说,将来要考协和医学院,当胸外科大夫。”
老人眼皮动了动:“哦?有志气。那你供得起吗?”
林小满手一顿,随即继续擦拭:“供得起。我现在有编制了,工资一百二十块,还有夜校补助二十,厂里那笔学习津贴也没停。再加上周末兼职记账,一年攒个八百不难。等他考上,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送。”
老人沉默片刻,忽然说:“我有个外甥在卫校当老师,回头我让他给你寄点复习资料。”
林小满心头一热,差点哽住:“赵伯,您……不用这么费心。”
“费什么心?”老人瞪眼,“我看人准。你这孩子,命苦,心不冷。该帮的人,就得拉一把。”
她低下头,只觉眼眶发热。这样的善意,像春雨落进干涸的土地,无声无息,却让她一次次挺直脊背往前走。
处理完3床,她又去巡视其他病人。走到7床时,发现床头空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她皱眉问隔壁病人家属:“李阿姨,6床那位老太太呢?”
“转ICU了。”对方叹气,“半夜心衰,抢救过来送到重症监护去了。”
林小满心头猛地一沉。那位老太太姓周,肺癌晚期,家里穷,儿子在外打工多年没音信,老伴早亡,住院费都是居委会凑的。她每次查房都拉着林小满的手说:“姑娘,我不怕死,我就怕走的时候没人给我合眼。”
她立刻跑去ICU门口打听情况。值班护士摇头:“刚稳定下来,现在不让探视。”
她站在玻璃窗外,看着里面密密麻麻的仪器,滴滴答答的心电监护声像针一样扎进耳朵。那一刻,她忽然想起母亲咳血那晚,自己背着她在雪地里狂奔的画面。那种无助、恐惧、绝望,至今还在骨子里留着印子。
“我不能只做个打针发药的护士。”她喃喃自语。
回到护士站,她翻开笔记本,在空白页写下一行字:**我要学急救护理,要懂危重症管理,要成为能救人于生死之间的人。**
晚上九点,她结束值班,没急着回家,而是去了医院图书馆。这地方偏僻,灯光昏黄,书架上大多是七八十年代的老教材。她在角落翻到一本《急诊医学概论》,泛黄的封皮上写着“内部资料,禁止外借”。她犹豫了一下,掏出工作证递给管理员:“我能复印吗?我保证按时归还。”
管理员抬头看了她一眼:“你是新来的那个林护士?听说你在夜校学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