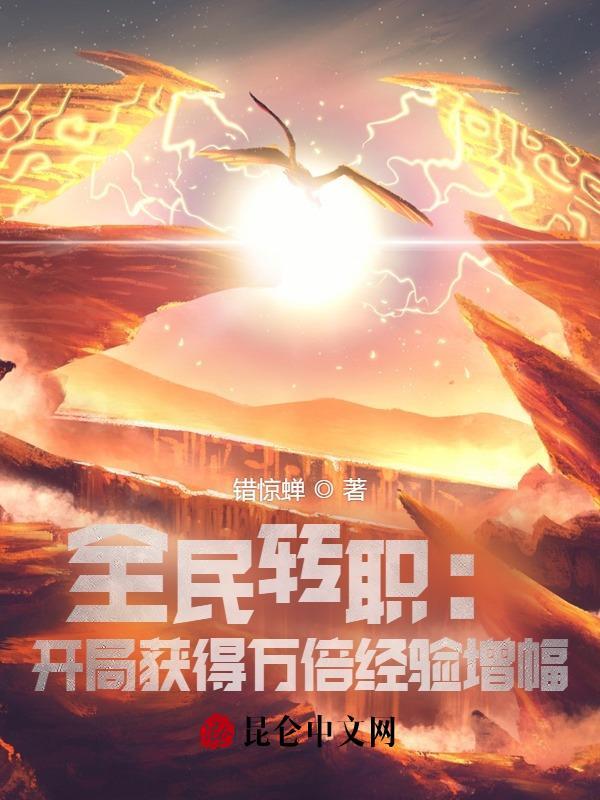鹅绒锁>大明:哥,和尚没前途,咱造反吧 > 第一千二百四十四章 脚底稳了心才不乱(第4页)
第一千二百四十四章 脚底稳了心才不乱(第4页)
白榆伸手一把把他住:“做什么慌?”
“我、我不是慌。”年轻人喘粗气,
“是来投奔的。我姓陈,陈同,做来回挑担的。我这几年挑米挑柴,腿倒是有,腰也硬,可走久了就心跳乱,半路想歇,越歇越不想走。今儿我在门口听了一会儿鼓,心里好像有条绳拽着我,就。。。。。。就来了。
“你想走?”朱瀚看他。
陈同点头:“我、我想走一百步不歇,再走两百步,再走??”
“别急。”朱瀚摆手,“先三十步。”
“我能多走。”陈同急。
“多了不稳。”朱瀚看他,“三十步不乱,你就能两百。”
陈同咬咬牙:“好。”
口吃学子把鼓抱到巷口,一时间大家的眼睛都落在陈同身上。
陈同把肩上的担子往地上一靠,又犹豫着提起:“王爷,要不要空手?”
“带着。”朱瀚道,“你平日怎么走,就怎么走。我们改的是你心里的秤,不是你肩上的。”
陈同点头。他站到绳头,吸了口气。
学子敲出第一下。陈同迈步,担子在肩上微微晃,他的脚却不慌。
走到第十步,他的眼睛里起了血丝;第十五步,他喉结滑动,像吞下一把沙;到第二十步,他忽然笑了,脚下反而轻了半分。
最后一步收住,他把担子一放,弯腰扶着膝盖,气喘如牛,却笑得像个孩子。
“几步?”有人问。
“正好三十。”口吃学子答,声音出奇的平稳。
“我还想走。”陈同抬头,眼里亮得惊人,“王爷,我明天还能来吗?”
“来。”朱瀚道,“不过明天,你帮人。你去教那些卖草鞋的,让他们把草鞋底绑得更贴脚,别让鞋帮松。脚底稳了,心才不乱。”
卖草鞋的瞪大眼:“我?我就会打绳结。”
“刚好。”朱瀚笑,“你看别人脚板,看看谁的脚外侧老磨破,谁内侧老起泡,然后再绑鞋。你不教他们走,只教他们穿。”
卖草鞋的抹一把脸上的汗,重重点头:“行!”
人群一阵笑声,巷口的窄墙似乎也被笑声撑开了半寸。
石不歪站在一旁看着,鼻翼微动,像闻到了旧时光里某种熟悉的味道。
“王爷,”韩定忽然开口,“我有个不情之请。”
“说。”
“能否,让太学的学生,也在这里帮忙?”
他转向那些穿着整洁的年轻人,“你们当先生,不光在屋里教字,今日便在巷口教脚。谁愿意?”
一时间,无人作声。
那个尖下巴少年迟疑了一下,竟第一个上前一步:“我愿意。”
韩定微微一惊,随即露出笑意:“好。”
少年转身,朝陈同伸手:“我姓顾,顾辰。你走的时候,如果肩上带风,你告诉我,我给你换一边垫布。”
陈同怔怔看着他的手,迟疑着伸上去:“我、我叫陈同。”
两人手掌一握,人群里又是一阵窃窃。
天色渐暗。白簪搬来油灯,挂在门额下。
灯火在风里摆动,映得每个人的脸都有了层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