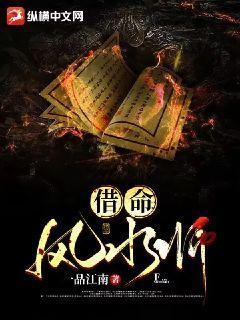鹅绒锁>腹黑如他,但男妈妈 > 7080(第33页)
7080(第33页)
我若不把剑还给?他,我还怎么心平气和?地去杀了他?
路婵却?越发无助道?:“可,可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他只说,自?己要去对付一个极厉害的对手,光靠曲水软剑不够,所以才要额外打造一把可以破了硬功的利剑,两剑齐用,才有可能打败那人。”
我登时眉心一紧,察觉出极大?的不对。
“他能为了这个敌人专门等?了三年,一定要打造一把新剑才去?那这人绝对不会是轻易可以杀死的对象。他怎能放弃了辛苦打造的新剑,拿了一把破落的旧剑就?直接上了呢?”
路婵奇怪道?:“可你才说过,八面重剑比我们的新剑还好啊……”
我假装没听到这话,只对着路婵道?:“路姐姐,你务必帮我想想他有可能去了哪里,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儿,晚一步的话……”
“会怎样?”
“晚一步,郭暖律那傻子?就?没命了!我必须去还剑!”
昨日恶贼今日是你
我通过“夜寒蝉”夫妇的细细回想,得出了一些蛛丝马迹,推测郭暖律此行要?去的地方,应该是屈山镇外一处名为蔡家村的荒村。
我立刻收拾行囊,骑了他特意留下的小墨奔袭而去。
像他这样的人,从?不会特意留着马儿给谁。
他能留下马,恰恰说明?他自己也觉得此行凶多吉少、未必能回,他不愿此等?骏马在自己死后就流离在外,就好?像他不愿一把宝剑因为主人遭难而?被弃荒野,所以他是特意换乘了“夜寒蝉”夫妇的一匹老马去的。
但他都留下小墨了,我能不用?么?
这时不是什么害臊的时候,为了追人,我带齐了伤药绷带不说,还?在自己的大腿上另缠了许多布帛棉花,在马背上也垫了厚厚的一层层缓冲棉花,然后我立刻翻身上马,准备去追人。
小墨也真是通人性,我抱着它的马脖子,学着郭暖律的样子轻轻在耳边说了一句“蔡家坡”,它就发出一声欢快的嘶鸣,如风如雷一般奔袭而?去,墨玉般的马蹄上下抖动如擂鼓,仿佛在地面上敲敲打打出了一截优美的音符。
且追且停地奔袭大半日,我终于到?了蔡家村。
村中的青壮年大多去了城内,因此村内多是老人,大多潦倒寂寞,村内也有一些庙宇古迹,可年久失修、残破不堪,连神像也被人盗走了首级,大概是用?于在古玩市场上变卖,可见此地荒落已久。
我一到?蔡家村,先问了几?个本地的村妇,就得知一名?与郭暖律形容相?似的男子,和另外一个看不见容貌的兜帽男子,一起去了村西边。
我赶忙奔马前去,果?然发现了两个人的脚印,渐渐追踪而?去,发现尽头指向的一处古庙。
此时天空微微暗沉,先是下起了星星点点的雨丝儿,跟着渐渐下大起来,像窒闷已久的空气一下子被人打开了话匣子,千般万种的话声儿都跟着雷电雨丝儿劈落下来,枯黄野草被风雨死死按住不说,树枝也被打得咯咯作响、微微颤抖。
雨像一层层墨似的,晕染着本就不亮的天空,我披着斗篷在这种雨色下,就好?像顶着一个墨水瓶子在走路,边走边洒的墨,满地都是黑泞泞的路。
不得已,我就站在高处的一棵树下,既躲着雨,也去俯瞰古庙门前的风与景。
这不看还?好?。
一看,我的心?都被抽紧了一些。
两个不怕雨也不怕冷的人站在庙门前,自觉充当了庙祝门神的角色。
一个是郭暖律。
一个是村妇口中的兜帽男。
可这两个人,尤其是那兜帽男身上散发出来的无形气势,真真像一座从?天而?降的高山,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压得都喘不过气儿来。
幸好?我不是普通人。
我还?是能健康喘气。
但心?中也有一股极度警惕的本能扩散开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毛骨悚然的感觉,直接从?脊背上蹿到?了我的脑门。
这是大敌!
这是看不清面目也能判断出的大敌。
这种强烈而?可怕的杀气,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只能从?你身上的肌肉一寸寸紧绷起来的可怖中才能感受到?。
难怪郭暖律特意寻了三年的材料,寻了“夜寒蝉”夫妇为他打造特制的武器,认为必须要?用?曲水软剑加上一把新剑,才来打破这敌人的硬功。
可这到?底是什么人?
在场之?人没有一个去回答我的问题。
郭暖律神色肃冷,如陈年积冰,并无一字可发。
那兜帽男也似厌恶了说话,更无一句废话撂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