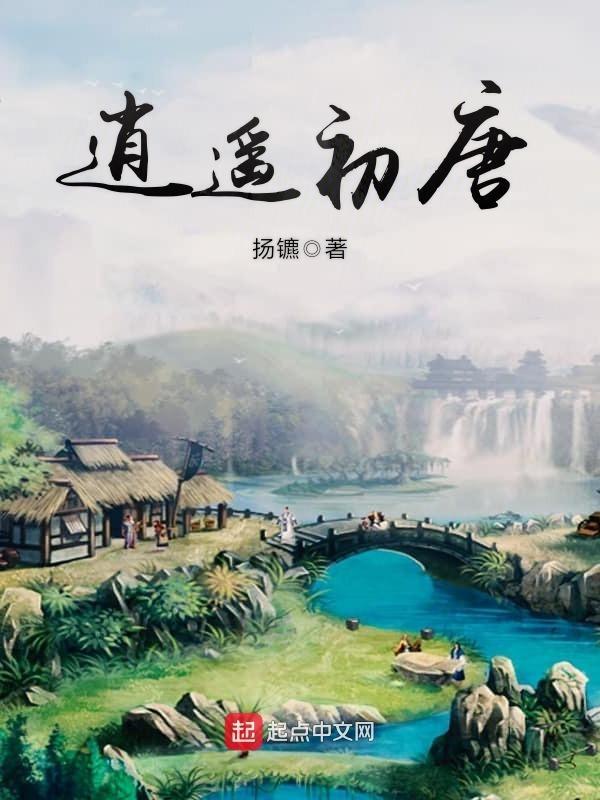鹅绒锁>食骨記 > 杭州西湖畔南宋桂花糖粥绣娘遗愿(第1页)
杭州西湖畔南宋桂花糖粥绣娘遗愿(第1页)
西湖暖粥:桂花糖粥里的师徒温情(增补完整版)
元代的杭州西湖,即便褪去了南宋都城的繁华,依旧藏着几分江南独有的温润。深秋时节,岸边的桂树缀满金黄的花穗,风一吹,细碎的花瓣便落在湖面上,随着水波轻轻晃荡,连空气里都飘着甜丝丝的桂香。柳娘的“柳氏绣坊”就开在西湖畔的巷子里,青石板路从绣坊门口蜿蜒到湖边,门前挂着的蓝布幌子上,用青线绣着“柳氏绣坊”四个字,针脚细密,一看便知是老手艺人的功夫。
绣坊里总弥漫着两种香气,一种是丝线与绸缎的清雅之气,另一种,则是熬煮桂花糖粥时的甜暖香气。每天清晨,柳娘都会先在绣坊后院的小灶上熬一锅桂花糖粥,用的是西湖边特产的圆糯米,泡足了十二个时辰,再用文火慢熬,等粥熬得浓稠绵密,再撒上自家晒制的干桂花,淋上一勺麦芽糖。粥刚出锅时,热气裹着桂香飘满整个绣坊,路过的行人闻到了,总会忍不住停下脚步,探头往里面望:“柳娘,今天的粥好了没?给我来一碗!”
陈墨是在去泉州港送完货后,特意绕到杭州的。他早听说杭州西湖的秋景最美,更听说柳氏绣坊的桂花糖粥是当地一绝,便想着来尝尝鲜,顺便看看能不能在《味魂录》里添一道新的美食方子。这天上午,他背着行囊走进绣坊,刚一进门,就被满屋子的绣品吸引了——墙上挂着绣好的西湖荷花图,荷叶上的露珠用珍珠米珠缀成,亮晶晶的像真的一样;桌上摆着未完成的绣帕,上面绣着几只嬉戏的鸳鸯,针脚灵动,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帕子上飞起来。
“客人是来买绣品,还是来喝粥的?”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陈墨回头一看,只见一位穿着青布衣裙的老妇人从里屋走出来,头发用青布巾包着,鬓角有些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却透着一股江南女子的温婉。这便是柳娘了。
“柳娘您好,我是来尝尝您的桂花糖粥的。”陈墨笑着说,目光落在了屋角的小桌上,桌上摆着几个粗瓷碗,旁边还放着一把银汤勺——那勺子和林阿妹的银汤勺有些像,只是勺身上刻的不是缠枝纹,而是几朵小小的桂花,一看就有些年头了。
柳娘点点头,转身去灶房盛粥。不一会儿,她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桂花糖粥走出来,粥碗里飘着一层金黄的桂花,甜香扑鼻。陈墨接过粥碗,拿起那把银汤勺,刚要舀起粥,突然发现勺身泛出淡淡的淡黄色光晕,像把秋日的阳光都揉进了银器里。他心里一动——上次在泉州港的阿妹糕铺,银汤勺也出现过类似的光晕,难不成这里也有不一般的故事?
他凑近些仔细看,光晕里竟映出个少女的身影——少女穿着淡粉色的绣娘裙,梳着双丫髻,手里拿着绣花针,正低头在绣绷上绣花,嘴角带着浅浅的笑,眼神专注又明亮。“柳娘,您看这勺子……”陈墨指着银汤勺,声音有些惊讶。
柳娘顺着他的手指看去,银汤勺上的光晕却瞬间散了,只留下冰冷的银器反光。她握着勺子的手微微一颤,眼神里闪过一丝伤感,过了好一会儿才轻声说:“许是阳光太足,晃了眼。”可陈墨分明看见,她的眼圈红了,像刚哭过一样。
陈墨没再多问,只是默默喝着粥。粥熬得确实好,糯米绵密,桂花香甜,一口下去,暖意在胃里散开,连带着心里都暖暖的。可他总觉得,这甜香里藏着一丝淡淡的遗憾,像西湖上空偶尔飘过的云,轻轻的,却挥之不去。
喝完粥,陈墨没有立刻走,而是和柳娘聊了起来。他说起自己在泉州港遇到的赛义德和林阿妹的故事,说起葡萄糕里藏着的跨族深情。柳娘听着,眼里的伤感更浓了,过了好久才开口:“你说的那个姑娘,让我想起了我的徒弟阿桃。”
阿桃是柳娘十年前捡回来的孩子。那时阿桃才八岁,父母在战乱中去世,她一个人在西湖边乞讨,柳娘见她可怜,便把她带回了绣坊,教她绣花。阿桃天资聪颖,学东西特别快,尤其是绣西湖的荷花,更是绣得栩栩如生。柳娘常说:“阿桃这孩子,是天生的绣娘,等我老了,这绣坊就交给她。”
去年冬天,杭州下了场罕见的大雪,绣坊里没有炭火,冷得像冰窖。柳娘的膝盖受了寒,每到夜里就疼得睡不着,只能抱着暖水袋蜷缩在床头。阿桃看在眼里,偷偷记在了心里。从那以后,她每天绣完活,就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用绣坊剩下的碎布料,一针一线地缝护膝。布料不够,她就把自己唯一的一件棉袄拆了,取出里面的棉絮填进护膝里;线不够,她就把平时攒下来的丝线接起来用。护膝的表面,她还绣上了小小的桂花图案——她记得柳娘最爱桂花,说桂花的香气能让人安心。
除夕那天,阿桃把缝好的护膝送给柳娘,护膝还是温热的,带着阿桃手心的温度。“师父,您戴着这个,膝盖就不冷了。”阿桃笑着说,眼里满是期待。柳娘接过护膝,摸到里面厚实的棉絮,看到上面精致的桂花绣纹,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那一夜,柳娘戴着阿桃缝的护膝,膝盖竟一点都不疼了,睡得格外安稳。从那以后,不管是冬天还是春天,柳娘都把护膝放在床头,像是握着阿桃的手,心里暖暖的。
去年,柳娘要过六十大寿,阿桃偷偷琢磨着要给师父准备一份特别的寿礼——一幅“西湖十景绣屏”。为了赶在寿礼前完成绣屏,阿桃每天都绣到深夜,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柳娘心疼她,劝她慢点绣,可阿桃总笑着说:“师父,我想让您生日那天,能看到最美的绣屏。”柳娘看着阿桃眼底的红血丝,想起去年冬天那副温暖的护膝,心里又疼又暖,只能每天多熬一碗桂花糖粥,放在阿桃的绣绷旁,让她能趁热喝。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柳娘寿辰前三天,阿桃突然咳起了血,倒在了绣绷前。柳娘发现时,阿桃手里还紧紧握着绣花针,绣绷上的“苏堤春晓”才绣了一半,旁边放着的桂花糖粥已经凉透了。医生说,阿桃是因为劳累过度,伤了肺腑,没救了。从那以后,柳娘就像变了个人,话少了,笑也少了,只有熬桂花糖粥的时候,眼神里才会多几分光彩——因为阿桃生前最爱喝她熬的粥,总说“粥暖,像师父的手”;也只有摸到床头的护膝时,她才觉得阿桃还在身边,没走。
“我每天都会熬一锅粥,想着阿桃要是回来了,就能第一时间尝到;我每天都把护膝放在床头,想着她要是冷了,也能像我一样,感受到这份暖。”柳娘说着,起身从里屋拿出一个布包,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副洗得有些发白的护膝,护膝上的桂花绣纹依旧清晰,“这是阿桃给我缝的护膝,我舍不得穿,只有想她的时候,才拿出来摸摸。我总觉得,她还在我身边,没走。”
陈墨看着那副护膝,指尖轻轻拂过上面的桂花绣纹,能感受到布料里残留的温度,仿佛还能看到阿桃深夜缝护膝的样子——灯光下,少女低着头,手指被针扎破了也不在意,只是一心想着要让师父的膝盖暖和起来。他心里酸酸的,突然明白,柳娘和阿桃的师徒情,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双向的守护:柳娘给了阿桃一个家,教她手艺;阿桃则用自己的方式,温暖着柳娘的岁月。
“柳娘,”陈墨犹豫了半天,还是开口了,“我在泉州港时,曾见过魂魄缠在珍视的物件上显形。阿桃姑娘最珍视的,不就是您和这绣屏、这护膝吗?说不定她的魂魄,就缠在这银汤勺、桂花糖粥和护膝里,等着有人帮她完成绣屏。”
柳娘身子一震,眼里闪过一丝希望:“真的吗?阿桃她……真的还在?”她紧紧握着手里的护膝,指节都泛了白,像是握住了最后一根稻草。
陈墨点点头,拿起那把银汤勺:“柳娘,您把勺子借我,我试着找找阿桃姑娘的念想。”
柳娘赶紧把勺子递给陈墨,眼里满是期待。陈墨握着银汤勺,在绣坊里慢慢走,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觉得勺子里似乎有股力量在指引着他。走到绣坊后院的绣架旁时,银汤勺突然又泛出淡黄色光晕,这次光晕里映出的,是绣架下的一个木盒子,盒子里放着一叠画纸,像是绣稿。
“是阿桃姑娘的绣稿!”陈墨激动地叫出声。他赶紧蹲下身,在绣架下摸索,果然摸到了一个小木盒。打开盒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十张绣稿,每张绣稿上都画着西湖的一景,从“苏堤春晓”到“断桥残雪”,画得细致入微,稿纸边缘还用工整的小楷写着“师父,生日快乐”,字迹稚嫩却充满了爱意。
“阿桃……我的阿桃……”柳娘接过绣稿,手指轻轻拂过上面的字迹,又摸了摸手里的护膝,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滴在绣稿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她捧着绣稿和护膝,像是捧着稀世珍宝,看了好久才开口:“阿桃这孩子,连绣稿都画好了,还想着给我缝护膝……她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陈墨看着柳娘伤心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他想了想,对柳娘说:“柳娘,阿桃姑娘肯定希望您能把这‘西湖十景绣屏’完成,也希望您能好好的,戴着她缝的护膝,喝着她爱喝的桂花糖粥,好好活下去。我虽然不会绣花,但可以帮您打下手,给您递丝线、绷绣布,您看行吗?”
柳娘抬起头,眼里满是感激:“谢谢你,孩子,要是能完成阿桃的心愿,我这辈子都感激你。”
接下来的日子,陈墨就留在了柳氏绣坊,帮柳娘完成绣屏。每天清晨,柳娘依旧会先熬一锅桂花糖粥,熬粥时,她会把阿桃缝的护膝放在灶旁的小凳上,像是让阿桃也能闻到粥香;陈墨帮着盛粥、洗碗,然后和柳娘一起坐在绣架前,柳娘绣花,陈墨就帮她整理丝线、换绣绷。柳娘的手有些抖,眼神也不如以前好了,绣一会儿就要歇一歇,每次歇的时候,她都会摸一摸放在身边的护膝,像是在和阿桃说话:“阿桃,师父今天绣得慢,你别着急,咱们慢慢绣。”
陈墨看着柳娘绣花的样子,心里满是敬佩。他想起阿桃生前绣荷花的样子,想必也是这样专注、这样认真;想起阿桃缝护膝时的样子,想必也是这样执着、这样温柔。有时候,他会忍不住问柳娘:“柳娘,阿桃姑娘绣荷花的时候,是不是也像您这样?她缝护膝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被针扎到手?”
柳娘点点头,脸上露出温柔的笑:“阿桃绣荷花,最擅长用‘虚实针’,绣出来的荷叶有层次感,像真的一样;她缝护膝的时候,手被针扎破了好多次,却从来没跟我说过,还是我后来看到她手指上的伤口,才知道的。她还说,等绣完‘西湖十景绣屏’,就再绣一幅‘荷花图’,挂在绣坊的正中间,让来买绣品的人都能看到;等冬天到了,再给我缝一副新的护膝,比上次的更暖和。”
陈墨听着,心里暗暗记下。他想着,等绣屏完成了,一定要帮阿桃完成这两个心愿:绣一幅“荷花图”挂在绣坊里,再给柳娘缝一副新的护膝,就像阿桃当年那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西湖十景绣屏”也渐渐有了雏形。“苏堤春晓”里的柳树抽出了新绿,“曲院风荷”里的荷花绽出了粉嫩的花瓣,“平湖秋月”里的月亮洒下清冷的光辉……每一针、每一线,都藏着柳娘对阿桃的思念,藏着护膝里的温暖,也藏着陈墨对这份师徒情的敬佩。
终于,在一个深秋的午后,“西湖十景绣屏”全部完成了。柳娘把绣屏挂在绣坊的正墙上,又把阿桃缝的护膝放在绣屏旁,阳光透过窗棂洒在绣屏和护膝上,丝线反射出五彩的光,护膝上的桂花绣纹也泛着温柔的光,美得让人移不开眼。“阿桃,绣屏完成了,你看到了吗?”柳娘对着绣屏和护膝轻声说,声音里满是温柔,“师父没让你失望,你给师父的寿礼,师父收到了;你给师父缝的护膝,师父还好好收着,暖和得很。”
就在这时,陈墨手里的银汤勺突然泛出淡黄色光晕,这次光晕里的少女身影格外清晰——阿桃穿着淡粉色的绣娘裙,手里拿着绣花针,身边放着一副未缝完的护膝,对着柳娘深深鞠了一躬,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然后身影渐渐淡去,消失在光晕里。银汤勺的光晕也随之散去,只留下一阵浓郁的桂花香气,那香气里,没了之前的遗憾,只剩满满的温情,像西湖畔的阳光,像护膝里的暖意,温暖又明亮。
“阿桃……阿桃走了……”柳娘看着光晕消失的方向,又摸了摸手里的护膝,眼泪又落了下来,可这次的眼泪里,没有了悲伤,只有释然和欣慰。她知道,阿桃看到绣屏完成了,看到护膝还好好的,终于可以安心地走了。
陈墨撰写《味魂录》:笔墨间的暖粥回响
那天夜里,陈墨回到柳娘为他安排的客房,桌上摆着一盏油灯,灯芯跳动着微弱的光,映得他面前的《味魂录》格外清晰。他翻开本子,前面几页写着泉州港的葡萄糕,字迹里满是对赛义德和林阿妹的敬佩。现在,他要写下杭州西湖的桂花糖粥,写下柳娘和阿桃的师徒情,写下那副藏着温暖的护膝。
他先从桂花糖粥的做法写起,笔尖落在纸上,脑海里却浮现出柳娘熬粥时的样子:她站在小灶前,手里拿着长柄勺子,轻轻搅动着锅里的粥,灶旁的小凳上放着阿桃缝的护膝,阳光洒在她的脸上,眼神专注而温柔,仿佛在呵护一件稀世珍宝。“桂花糖粥,取西湖圆糯米三斤,清水浸泡十二时辰,文火慢熬两个时辰,至粥浓稠绵密,撒干桂花半两,淋麦芽糖一两……”他一边写,一边想起柳娘说的,阿桃生前最爱在熬粥时帮她撒桂花,总说“师父,我撒的桂花最香,能让粥里都藏着西湖的味道”;想起阿桃深夜缝护膝的样子,手指被针扎破了也不在意,只是一心想着要让师父暖和。陈墨的嘴角不自觉地向上扬,心里却有些发酸——阿桃帮柳娘撒桂花、缝护膝,哪里是为了让粥更香、让护膝更暖,分明是想把自己的心意,都藏进这些日常的小事里,陪着师父走过每一个日子。
写到“文火慢熬两个时辰”时,陈墨的笔顿了顿,眼前突然闪过两幅画面:一幅是阿桃穿着淡粉色的绣娘裙,站在小灶旁,帮柳娘添柴火,两人偶尔对视一眼,都会露出温柔的會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