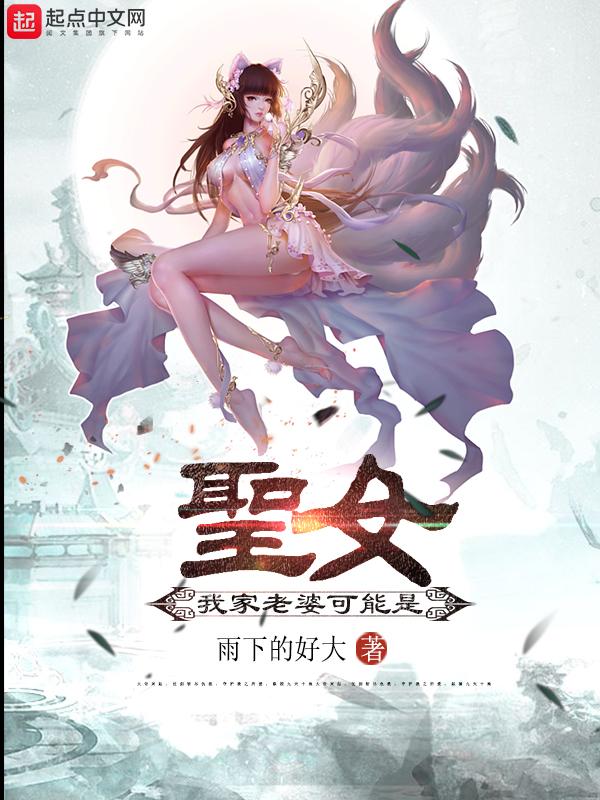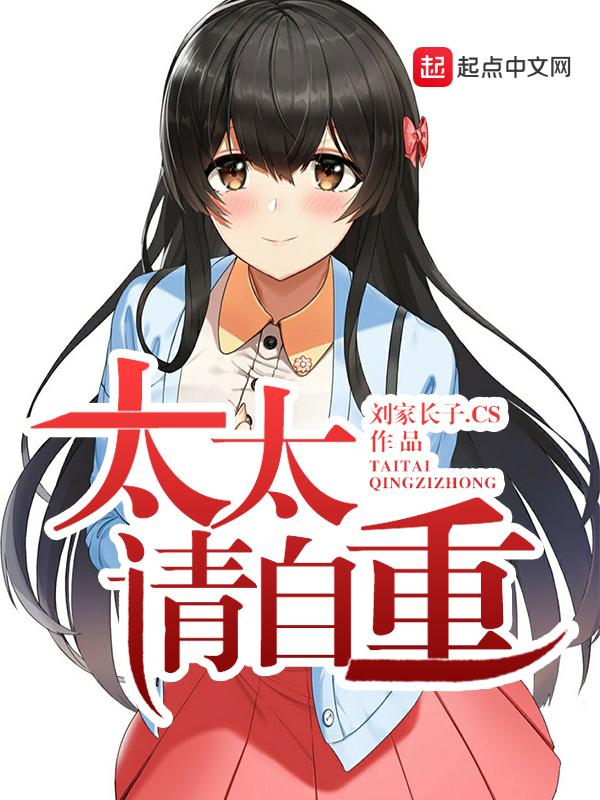鹅绒锁>天幕直播朕的恋爱史 > 父子对峙(第2页)
父子对峙(第2页)
“敬着念着?瞧瞧你干的好事!‘圣祖’皇帝?好大的威风!”皇帝怒极反笑,“说说吧,将你父皇我‘道德绑架’至此,感觉如何?”
“父皇,您也说了,那是‘圣祖’干的事,和现在的黎昭有什么关系?”黎昭一脸无辜。
“胡搅蛮缠!”皇帝一掌拍在案上,“照你所说,若无这天幕,你便不会行这为庞迎伸冤、逼迫君父之事了?”
黎昭心下一横,知道此刻唯有坦诚:“不瞒父皇,即便没有天幕,来年会试,也确是儿臣计划发难之机。”
“好,好得很!真是朕的好儿子啊,古有佛祖割肉喂鹰,今有你黎昭为民杀兄迫父,就不怕有朝一日被鹰啄了眼?”
面对皇帝饱含讥讽与压迫的质问,黎昭深吸一口气,他眼中的嬉笑尽数敛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沉静与通透。他再次拱手,这一次,姿态是前所未有的郑重。
“父皇的比喻精妙,但儿臣以为,二者有本质不同。”
“哦?”皇帝冷哼一声,倒想听听这“逆子”又能吐出什么象牙。
“佛祖割肉喂鹰,是舍己身以全他命,是慈悲,亦是牺牲。而儿臣所为——”黎昭抬起头,目光清亮,不闪不避地地迎上皇帝锐利的视线,“并非是要牺牲自己或皇室去成全谁,而是要重塑规则,奠定基石。”
他斟酌着词句,试图将超越时代的理念,装入这位古代帝王能理解的容器:“儿臣并非想当圣人,也当不了圣人。”
”儿臣只是想明白一个道理:统治的根基,长远来看,不在严刑峻法,不在权谋制衡,而在人心向背与朝廷公信。朝廷的制度信用,是天下人对‘公平正义’这四个字最朴素的期待。”
“人心向背,在于朝廷是否将百姓的诉求真正放在心上。而百姓所求不过是吃饱穿暖,安稳一生。纵观史书,王朝末年衰亡无不伴随着起义,新王朝的建立也是伴随着起义,无论兴衰,苦的都是百姓。”
“若百姓能安稳度日,谁会去参与起义,这就是民心。父皇,您是开国之君,亲眼见过前朝如何倾覆,我大晟如何崛起,其中关窍,您比儿臣体会更深。”
听到此,皇帝眉头微皱,“继续说。”
“迫父并非本意,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让天下人看到,朝廷有自洁之能,皇族有不徇私情,容人之量,法度有至高之威!让‘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再是一句空谈!如此,百姓方能归心,士林方能效死。”
他顿了顿,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金石坠地:“儿臣不是要自己做圣人,而是要请父皇,与我朝律法,一同成为那不可逾越的‘规矩’本身。”
“儿臣心里有父皇,所以不愿见父皇的圣明,被些许蠹虫拖累。儿臣眼里有江山,所以不能坐视国本动摇。若此举让父皇震怒,儿臣愿领责罚。但若重来一次。。。。。。”黎昭目光坚定,毫无退缩,“儿臣,依然会做。”
殿内陷入一片死寂。黎昭的话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深潭,激起的不是水花,而是无声却汹涌的暗流。
皇帝凝视着下方这个熟悉又无比陌生的儿子,,能说出这番话,绝非一时意气。这几乎是将那份不容于世的野心,明晃晃地摆在了台面上。
“你这番话,”皇帝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山雨欲来的压迫感,“将你的太子皇兄置于何地?又将朕,置于何地?你就不怕。。。。。。”
“父皇,”黎昭罕见地打断了皇帝的话,语气却异常平和,“您不会那么做的。您是圣明之君,深知王朝未来的命运系于您一念之间。您亦是慈父,天幕一出,儿臣已无退路,不争便是自寻死路。至于太子皇兄,他仁厚贤德,于儿臣更有兄弟之谊。无论是现在,还是天幕预示的未来,儿臣都绝不会对皇兄出手。”
“现在知道兄弟血缘了?”皇帝挑眉,“那楚王,难道就不是你的兄长了?”
“父皇明鉴,”黎昭的声音果断而坚决,“三皇兄所作所为,天理难容。他需要为自己犯下的罪孽,付出应有的代价。”
最终,皇帝缓缓靠回龙椅,看不清神色,只是挥了挥手,声音听不出喜怒:
“滚下去。即日起,你去大理寺报道,负责审理科举舞弊案。”
他深深一揖:“儿臣,告退。”黎昭知道,今日这场风暴,暂时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