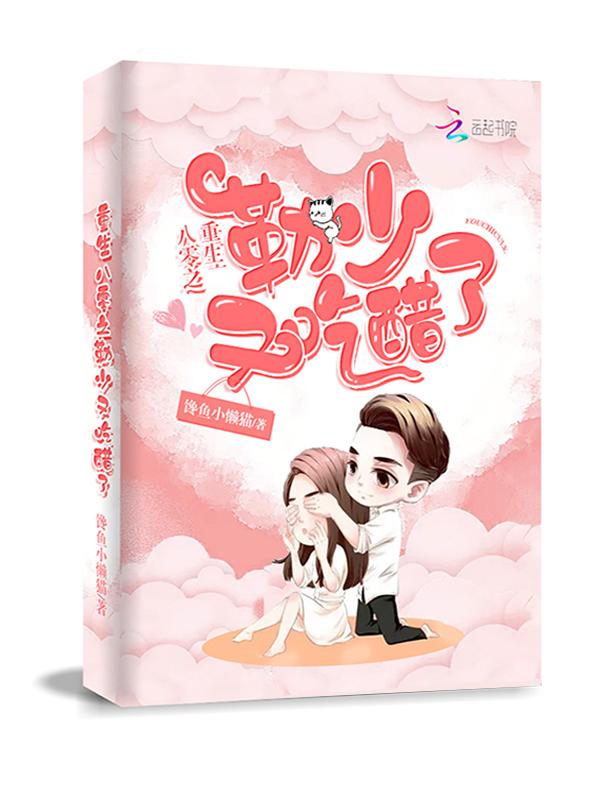鹅绒锁>清冷无情?他老婆腰都折了算什么 > 第343章 九千岁二十一(第3页)
第343章 九千岁二十一(第3页)
大的,如黄豆,为母蛊,小的,如米粒,为子蛊。
萧寂將手指塞进那罐口中,小的那只黑色甲虫便顺著萧寂的指尖,爬上了他的手腕,张牙舞爪咬破了萧寂的皮肤,钻进血肉,消失不见。
皇帝见状,苍老的手指也塞进了罐口,大的那只甲虫,也同样迅速钻进了皇帝的腕间。
细小的伤口甚至连血液尚未来得及溢出,便已经癒合了。
萧寂看了看自己的手腕,对皇帝躬身行礼:
“天色已晚,臣便不打搅陛下歇息了。”
说完,既没看皇帝脸色,也没管祁隱年,便转身离开。
只是与祁隱年擦肩而过时,髮丝划过了祁隱年的脸颊。
祁隱年眼下心里一团乱麻,但为了不引人猜忌,到底还是又跟皇帝说了会儿没用的屁话,这才离开崇华殿。
明面上,是回了昭阳殿,实则前一秒刚进了昭阳殿的门,后一秒,便顺著窗子跃了出去,直奔司礼监而去。
萧寂就站在窗边,將祁隱年接了个满怀。
祁隱年有些时日不曾与萧寂亲近了,但此刻却无暇顾及此事,从萧寂怀里挣脱出来,伸手抓住他的手腕:
“怎么样了?”
萧寂知道祁隱年担惊受怕了一晚上,刚刚眼见著他蛊虫入体却无力反抗,心中不指不定得多难受。
他安抚地摸了摸祁隱年的后脑:
“没事,给我抱抱。”
祁隱年红了眼眶:“是我没用,我……”
萧寂打断他:“小不忍则乱大谋,方才的情形,你没轻举乱动,便是上策。”
“我一直担心你会打乱我的计划,眼下看来,殿下还是靠得住的。”
祁隱年的確想了很多。
或是不管不顾地杀了皇帝,丟了江山,带著萧寂亡命天涯。
或是不小心將那蛊打翻在地,趁机將其踩死。
事后皇帝若是发难,他便说自己患了癔症,突发恶疾。
任皇帝將气撒在他头上,饶了萧寂。
但所有的衝动,却最终都被萧寂一个警告的眼神,扼杀在了摇篮里。
祁隱年盯著萧寂看不出任何异样的手腕:
“萧寂,如果你的计划,是用你自己换我事成,我必不会放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