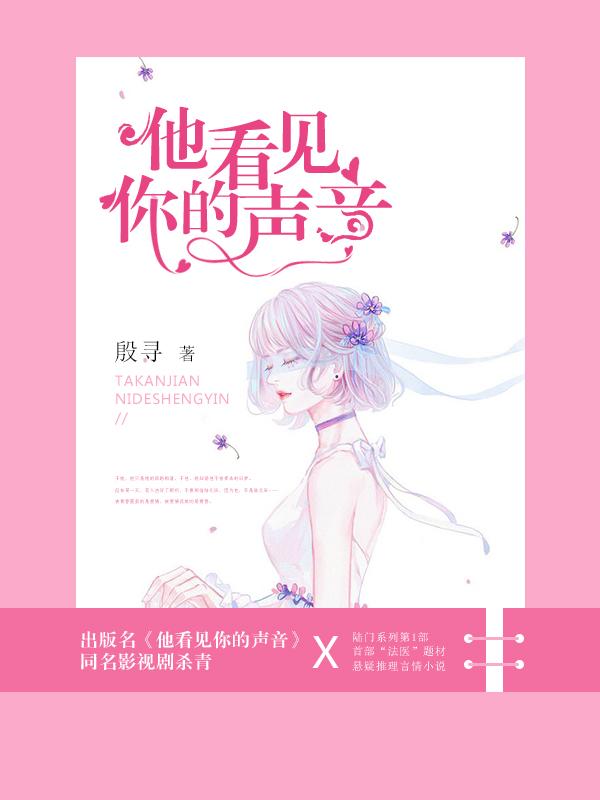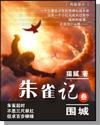鹅绒锁>夺回享福命,炮灰长媳夫贤妻贵 > 第468章(第1页)
第468章(第1页)
第468章
只见一位身着素色锦袍的老者慢慢走来。
看着大概六十岁左右,鬓角有些白发,面容清瘦,目光温润澄澈,嘴角含着微笑。
气度谦和,周身笼罩着一层书香沉淀下来的光华。
正是当朝太傅、清流领袖、天子之师——崔泓,崔玉章。
他先是与厅中几位熟识的文人颔首致意,态度亲切自然,随即目光便落到了杜仁绍与李梵娘身上。
“镇国公,医仙娘娘,大驾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崔泓走上前,语气温和真诚,没有半点架子。
“二位在江南力挽狂澜,救民于水火,实乃是家国之幸运,老夫钦佩已久。今日终于见到了二位,果然名不虚传。”
他的目光在杜仁绍身上停留一瞬,“国公爷英武不凡,正气凛然。”
又转向李梵娘,笑容和蔼:“娘娘仁心圣手,更难得如此年轻,真乃我朝的福气。”
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表达了赞赏,又给了二人尊重,让人挑不出半点错处。
杜仁绍与李梵娘也礼貌回敬:“太傅过誉,愧不敢当。太傅乃是天下文宗,陛下之师,我辈楷模。”
“诶,今日只是私宴,不必拘泥礼数。”崔泓笑着摆手,亲自引他们入座,位置安排得很周到,既显的尊重,又不至于太过突兀。
宴会开始,丝竹声起。
侍女们奉上茶点,酒是陈年佳酿,菜是时令珍馐,烹饪到位,摆盘雅致,无一不体现出崔家极高的生活品味和底蕴。
席间,崔泓谈笑风生,与在座的文人们探讨诗词歌赋,品评书画古玩。
宴会的气氛始终维持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中。
崔泓学识渊博的程度令人叹服,从《诗经》的草木之名到《本草纲目》的药材辨析,他都能信手拈来。
与李梵娘探讨时,仿佛只是一位醉心学问的长者。
他甚至能准确说出杜仁绍几年前在西北某场战役中的战术调度,分析得头头是道,言语间充满了对武将不易的理解与钦佩。
“国公爷当年以少胜多,扼守狼牙隘口,真是妙,诡道也,手下是将士血汗,上到社稷安危,不是我们能纸上谈兵的人可以随便议论的。”他举杯向杜仁绍示意,眼神恳切。
杜仁绍心中警铃大作。
此人若为敌,实在太可怕。
他不仅能投你所好,更能完美消除你的戒心。
他举杯回敬,“太傅过誉了,守卫疆土,是我的分内之事,比不上太傅辅佐陛下,教化天下,乃定国安邦之根本。”
崔泓呵呵一笑,捋着胡须摇头:“国公爷这话说的折煞老夫了,文治武功,就像是车的两个轮子,鸟的双翼,缺一不可。”
“陛下能有国公与夫人这样的肱骨,实乃大胤之福。”
他巧妙地将话题再次引回对皇帝和朝廷的忠诚上。
李梵娘安静地坐在一旁,面上带着得体的笑,心思却飞速转动。
她仔细观察着崔泓的每一个表情,他说话时的语气停顿,他举杯时指尖的弧度,他听人说话时眼神的专注。
太完美了,反而显得不真实。
就像一幅画,笔笔到位,却独缺真实。
她注意到,每当谈到某些特定地域的药材流通或民间偏方时,崔泓的知识储备似乎更深了,甚至能说出一些连太医署典籍都未必记载过的冷僻用法。
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文人雅士该知道的。
然而,每当李梵娘试图把话题引的更深,比如某种稀有药材的具体产地、采集时节,或者是某些传闻中带有禁忌的古老药方时,崔泓又会不着痕迹地错开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