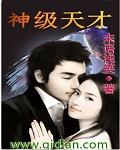鹅绒锁>当过明星吗,你就写文娱? > 第二百一十三章 一次不够得两次(第2页)
第二百一十三章 一次不够得两次(第2页)
林晚说不出话,只能紧紧抱住她。
当晚,余惟做了一件大胆的事。他将所有采集到的侗族大歌片段进行空间化处理,利用定向扬声器技术,在鼓楼四周布置音响阵列,使得歌声仿佛从空中飘落,又似自地底升起。然后他邀请全村人围坐一圈,宣布:“现在,请你们闭上眼睛,听一听一百年前的自己。”
音乐响起那一刻,许多老人不由自主跟着哼了起来,有些人甚至站起来,颤巍巍地摆动身体。一个中年男人突然跪倒在地,痛哭失声??那是他母亲生前最爱的曲子,他已经三十年没听过了。
第二天,十几个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打来电话:“我们想回来学唱歌。”
这不是奇迹,余惟知道,这只是因为有人终于愿意停下脚步,认真去听。
离开侗寨后,他们继续向南,进入广西边境的一座废弃麻风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曾隔离过上百名患者,围墙高耸,外界视之如瘟疫之地。尽管疾病早已根除,村庄荒废多年,村民后代仍背负污名,无人敢提那段历史。
余惟和林晚在这里遇到了陈阿婆,当年十三岁被送来,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唯一留守者。她带他们走进一间塌了一半屋顶的老屋,指着墙壁说:“你看,这些划痕,是我们数日子留下的。”
墙上密密麻麻刻着横线,每十道一组,旁边还用炭笔写着“想妹”“盼信”“今日无药”之类的短句。
“那时候不能写字寄出去,”陈阿婆低声说,“我们就用指甲刮墙,一边刮一边念。我说一句,隔壁阿强就敲一下墙回应。后来我发现,墙真的记得话。”
余惟立刻架设设备,用接触式麦克风扫描墙面。经过降噪处理,他们竟然提取出大量微弱振动信号??有咳嗽、哭泣、祷告,甚至还有一段男女对唱的粤剧选段,断续却深情。
他们将这段音频命名为《墙语?隔离年代》,并在当地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倾听仪式”。邀请原住民及其子孙回到故地,戴上耳机,听着父辈在绝望中仍努力发声的痕迹。一位中年妇女听完后扑倒在墙边,嘶喊:“爸!我听见你了!我一直以为你恨我丢下你……可你一直在唱歌啊!”
那一刻,余惟终于明白周志民当年为何坚持要把声音带到矿井、工地、养老院??因为真正的治愈,从来不是遗忘痛苦,而是让痛苦被听见。
项目影响力不断扩大,“声音驿站”陆续在全国设立二十七个站点,涵盖边疆哨所、海岛灯塔、地下煤矿、留守儿童学校等地。教育部采纳建议,在“倾听课”基础上增设“声音日记”课程,要求学生每周录制一段身边的真实声音,并撰写聆听感悟。有孩子交上来一段录音:深夜厨房里妈妈切菜的声音,背景是父亲压抑的咳嗽。他在作文里写道:“以前我觉得家里很吵,现在才懂,那是他们在用力活着。”
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某权威媒体发表评论文章,题为《警惕“声音泛滥”:当一切都被记录,隐私何处安放?》。文中质问:“我们是否正在制造一个新的监控文明?当连咳嗽、私语、梦呓都被采集,人性的最后一层遮蔽是否也将消失?”
舆论哗然。支持者认为这是杞人忧天,反对者则呼吁立法限制声音采集范围。
余惟没有回避。他在一次公开论坛上直言:“我们恐惧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人心的冷漠。如果一个人不愿倾听,哪怕全世界安静如死,他也听不见爱;如果一个人愿意倾听,哪怕噪音如潮,他也能听见心跳。问题不在录音,而在我们有没有勇气面对真实。”
他顿了顿,补充道:“我采集声音,从不偷录。每一次按下录音键,我都先问一句:‘我可以听你说话吗?’得到允许,我才开始。这才是尊重的起点。”
这场辩论最终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声音权益保护条例》草案出台,明确界定“声格权”概念:每个人对自己的声音拥有所有权、使用权与被遗忘权。任何机构或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模仿、商用或公开他人语音数据。
2028年冬,“人间和声”全球巡展在巴黎开幕。展厅中央是一座由数千个微型扬声器组成的立体装置,外形酷似人耳。参观者走入其中,便会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碎片:非洲草原上的鼓声、北极冰川断裂的轰鸣、孟买贫民窟孩童的笑声、东京地铁早高峰的脚步节奏……每一段都配有讲述者照片与简短故事。
法国《世界报》评价:“这不是一场展览,而是一次集体疗愈。它提醒我们,全球化不仅是资本与信息的流动,更是情感与记忆的共振。”
闭幕式上,余惟播放了一段从未公开的音频。那是他在排爆部队最后一天录下的:一群战士围坐在篝火旁,轮流讲自己最害怕的事。有人说怕炸不死敌人自己先死,有人说怕父母接到阵亡通知书时崩溃,还有一个年轻的兵哭了:“我最怕退伍回家,发现自己已经不会好好说话了……整天绷着,连笑都像在执行任务。”
音频结束,全场寂静。
良久,一位法国老兵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说:“谢谢你们让我知道,原来别的国家也有士兵不敢哭。”
回国途中,余惟收到一条短信,来自深圳那位AI训练师小杨。他曾参加“反向聆听”工作坊,如今已转岗做用户体验设计。短信写道:“昨天我女儿出生了。我录下了她第一声啼哭,没上传云端,也没做声纹分析。我只是每天晚上放给她听,告诉她:这是你来到这个世界时,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你要记住,你是被期待的。”
余惟靠在舷窗边,望着云海翻涌,忽然想起那个被他写进笔记本的问题:“如果所有声音都被记录了,我们会不会失去倾听的能力?”
现在他有了答案:不会。只要还有人愿意为一声啼哭停下脚步,为一句遗言屏息凝神,为一段沉默长久驻足,倾听就不会消失。
飞机降落北京首都机场时,天刚蒙蒙亮。他拖着行李走出航站楼,迎面撞上一群举着相机的学生。为首的女孩激动地问:“余老师,您觉得未来还会有什么新的声音被发现吗?”
他笑了笑,指向远处清洁工扫地的沙沙声、出租车启动的引擎声、候鸟掠过城市上空的鸣叫。
“你看,”他说,“下一秒,就是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