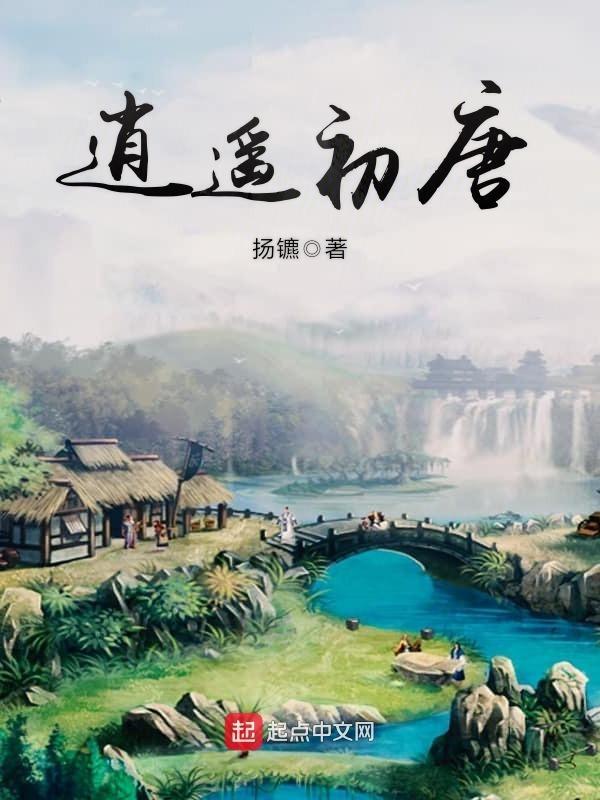鹅绒锁>七零易孕娇娇女,馋哭绝嗣京少 > 第581章开始捉弄人(第1页)
第581章开始捉弄人(第1页)
马生平在门外,刚好听到大姑这么说,他早就猜到是亲戚挑拨的,没想到大姑这么过分,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
父母也是蠢,咋能信了这鬼话?
想到这里,马生平再也控制不住,推开门对着大姑破口大骂。
“我说我爸妈怎么非要没事找事,原来是你给编排的?你儿子不是个好东西,吃喝嫖赌找了个媳妇,人家跑了,你就见不得我们家好?现在挑拨我跟大红,你还是不是人,亏我还叫你一声姑姑呢,我呸!”
马父听到儿子这么骂自己姑姑,立刻。。。。。。
夜色如墨,加林村的风裹着沙砾拍打帐篷。卓玛躺在行军床上,听着外面发电机低沉的嗡鸣,那是李岩带着两个队员连夜架设的小型太阳能储能系统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在寂静高原上显得格外清晰,像心跳,又像某种承诺。
她翻了个身,手机屏幕亮起,是江倩倩发来的消息:“纽约那边有个基金会想资助‘姐妹微校’项目,但他们要求看到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报告。”后面还附了一张图表截图,标题写着《女性教育投入与地区生育率、儿童死亡率的相关性分析》。
卓玛轻轻叹了口气,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回了一句:“告诉他们,我们不卖数据,只讲故事。但每个故事,都是真实改变的证据。”
放下手机,她起身披衣走出帐篷。月光洒在雪线上,银白一片,仿佛天地之间只剩下这一片纯净。远处寺庙的金顶在月下泛着冷光,那老僧侣的身影似乎仍伫立在台阶之上,口中念诵经文,语调苍凉。
第二天清晨,第一堂课如期开始。
教室是临时腾出的一间牛棚改建的,地面铺了草席,墙上挂着一块黑板??还是从措玛村带过来的旧物。十五个女孩陆续走进来,最小的不过八岁,最大的已近二十,眼神里混杂着好奇、羞怯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
“我叫卓玛。”她站在讲台前,用藏语缓缓开口,“我不是神,不是佛,也不是妖魔。我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曾经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女人。”
孩子们安静下来。
“你们知道卫生巾是什么吗?”她拿出一片展示给所有人看,“它不是邪物,不会招灾,也不会让牲畜生病。它是用来接住月经血的,让女人不必再用破布、草灰甚至羊皮去捂着流血的身体。”
底下一阵骚动。有女孩低头咬唇,有母亲模样的妇女站在门口怒目而视。
“我们村里有个姑娘,十六岁那年第一次来例假,以为自己中毒快死了,躲进山洞三天不敢回家。”卓玛继续说,“她阿妈说她是‘脏的’,让她睡牛圈。后来她真的病了,高烧不退,差点丧命。医生说,是因为感染。”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脸:“你们愿意自己的女儿也这样吗?”
没有人回答,但有人悄悄抹了眼泪。
中午时分,一名年轻女子偷偷溜进营地,怀里抱着一个布包。她是昨晚听了一节课后悄悄回来的,名叫格桑拉姆,十九岁,去年刚生下一个死胎,丈夫因此将她赶出家门,说她“命硬克子”。
“老师……我能学写字吗?”她声音颤抖,“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流产?是不是我真的有罪?”
卓玛握住她的手,掌心相贴,暖意传递。“你没有罪。你的身体很辛苦,但它不是诅咒。我们会教你认字,也会请医生远程为你检查身体。你值得被好好对待。”
当天下午,达瓦央宗组织了一场“身体工作坊”。她们用橡皮泥捏出了子宫、卵巢、输卵管的模样,一边讲解,一边鼓励女孩们提问。起初没人敢说话,直到一个小女孩举起手,怯生生地问:“那……每个月流血,会死吗?”
全场哄笑,随即又安静下来。
“不会。”卓玛温柔地说,“就像大地每年都要经历冬去春来,我们的身体也有节律。这是自然,不是惩罚。”
傍晚,篝火燃起。这次不再是敌意的目光,而是三三两两的母亲带着女儿围坐过来。她们低声交谈,有人开始讲述自家女儿因早婚被迫辍学的经历,有人说起亲戚家的女孩难产而亡,连救护车都进不了山。
李岩打开投影仪,连接卫星网络,在白色帐篷上播放了一段视频:云南山区一位女医生蹲守产房三十年,亲手接生两千多名婴儿;贵州一位乡村教师坚持送教上门,帮助六十多名失学女孩重返校园。
画面最后定格在一个小女孩握笔写字的瞬间,镜头拉近,纸上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我要活。
人群沉默良久。
终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拄着拐杖站起来,颤巍巍地说:“我活了七十二年,头一回听说女人还能这样活。”她转向身边儿媳,“把孙女送来上学吧。我不信什么‘读书坏了德行’,我要她活得明白。”
那一刻,卓玛眼眶湿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