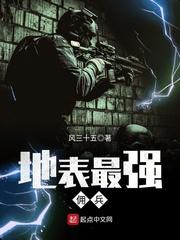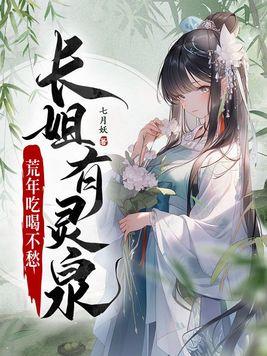鹅绒锁>相国在上 > 238按图索骥(第1页)
238按图索骥(第1页)
府衙,同知厅。
叶庆早已等候在此,一见薛淮进来便上前相迎。
通过这大半年来的合作,尤其是这次设局抓捕乱党重要人物、成功抓住妖教的蛛丝马迹,这对叶庆来说又是一桩极其重要的功劳。
靖安司。。。
春风拂过太湖,湖面波光粼粼,如碎银洒落。沈砚之坐在院中石凳上,手中执笔,在宣纸上缓缓写下一行小楷:“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字迹清瘦挺拔,一如其人。苏婉清端来一盏新焙的碧螺春,轻轻搁在案边,笑道:“又写你的《治要录》?这已是第三卷了。”
“闲来无事,整理旧思。”他搁下笔,抬眼望她,“你说,后人若读此书,会信其中所言吗?”
“若天下太平,则信;若乱世再起,则更信。”她倚着他肩头,“人心总在危难时才想起良药苦口。”
他轻笑一声,正欲答话,忽闻院外脚步细碎,似有孩童奔来。紧接着,篱门被轻轻推开,一个约莫十岁的男孩探头进来,手里攥着一本破旧册子,怯生生道:“老……老爷爷,我能借您这儿抄会儿书吗?我娘说,这是您写的《户政辑要》,学堂先生讲不明白,我想自己琢磨。”
沈砚之怔了怔,接过那册子一看,封皮已磨得发白,页角卷曲,显然翻阅甚勤。他翻开一页,见空白处密密麻麻写着稚嫩批注,虽错字连篇,却一笔一划极为认真。
“你叫什么名字?”他柔声问。
“阿禾,姓陈,姑苏人。”孩子低头搓着手,“爹早年饿死在逃荒路上,娘靠织布养我。去年官府按您定下的‘均田则赋’重划地籍,我们家分到了三亩半水田,今年就能吃饱饭了。先生说,这都是因为当年有个大官儿,不怕得罪人,硬把豪强占的地退了出来……他还说,那官儿叫沈砚之。”
沈砚之沉默良久,终是将书还给他,点头道:“坐吧,就在这儿抄。若有不懂的,我可以讲给你听。”
阿禾惊喜抬头,不敢置信:“真……真的可以吗?”
“嗯。”他微笑,“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抄完之后,不准叫我老爷爷。”他故意板脸,“我还没那么老。”
阿禾扑哧一笑,连忙应下,搬了小凳坐下,埋头抄写。阳光穿过桃枝,斑驳洒在纸面,映着他专注的侧脸。苏婉清看着这一幕,眼角微润,低声道:“你瞧,你的字,比圣旨还管用。”
“不是我的字管用。”他望着少年,“是百姓记得。”
午后,林修再度悄然来访,换了一身布衣,扮作游方郎中。他在院外远远望见沈砚之正教阿禾写字,久久未动,直到暮色四合,才叩门而入。
“相爷,北疆急讯。”他压低声音,“沈澈现身了。”
沈砚之正在灯下校对书稿,闻言只抬了下眉:“何处现身?”
“朔州边境,率三千骑兵突袭守军营寨,夺粮草辎重而去。旗号打的是‘正统嗣君’,并发布檄文,称先帝遗诏确遭篡改,太后临终亲口承认,当今天子系庶出冒立,无权继统。已有两州守将动摇,暗中遣使联络。”
苏婉清倒茶的手顿住:“他当真活着?”
林修沉声道:“容貌与当年皇榜画像相符,身边随从亦多为旧日东宫侍卫。更关键的是……他手持半枚玉鱼符,与宫中所藏另一半可合。”
沈砚之缓缓放下笔,闭目片刻,忽而问道:“皇帝如何应对?”
“震怒,欲亲征。但朝中分裂,一派主张剿灭叛逆,另一派竟提议迎归‘太子’,以和解天下。御史台联名上奏,请召您回京主持大局。”
“又是这一套。”苏婉清冷笑,“知道您不会回来,便造势逼宫,想借您的名望压服异己。”
沈砚之睁开眼,目光清明如初雪:“他们忘了,真正的权力,从来不在谁喊得多响,而在制度是否稳固。”
他起身踱步至墙边,墙上挂着一幅手绘地图,标注着各州赋税、兵备、漕运路线。这是他十年隐居间,凭记忆与各地访客口述所绘,竟比户部档案更为详尽。
“林修,你告诉我,地方官员是否仍依《考成法》按月上报政绩?”
“是。”
“盐铁专营可曾松懈?”
“未曾。江南十二仓依旧三年轮储,灾年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