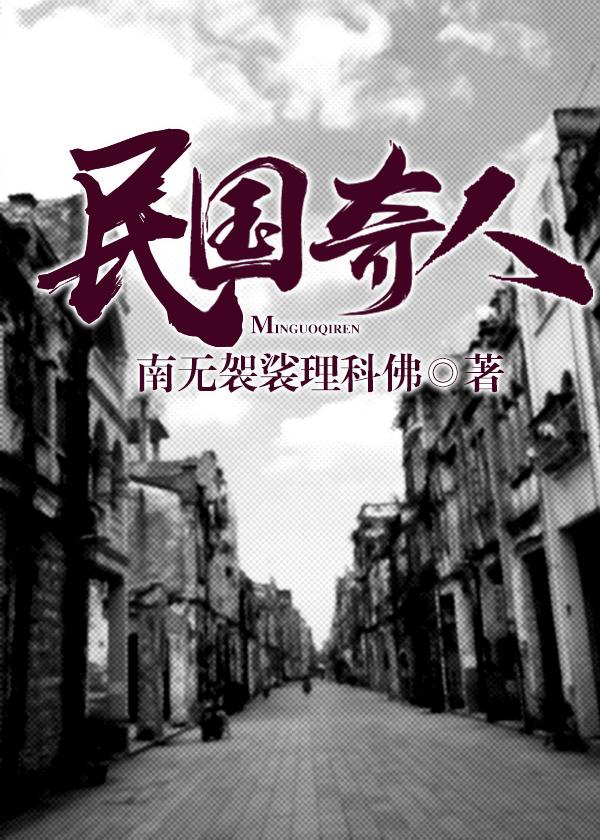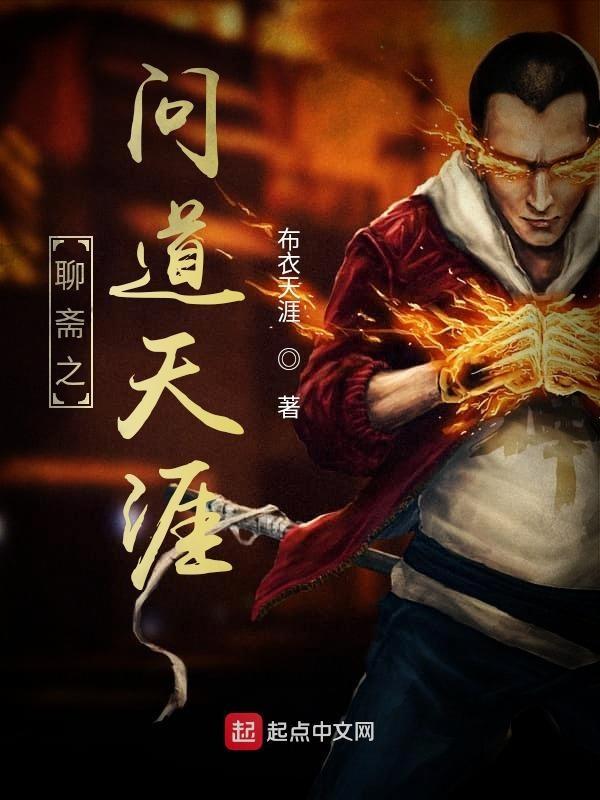鹅绒锁>诡目天尊 > 第 432 章 安 置 灵 脉(第1页)
第 432 章 安 置 灵 脉(第1页)
三人回到洞府之中,姜启取出阵牌隔绝外界,他这才说道:
“墨师姐,听妖师妹,我还有一事想与你们商量,我从真龙宗那里换来了两条极品灵脉,你们觉得安放在哪里合适?”
闻听此言,墨娆心中不由得一惊,眸中闪过一抹讶异之色,轻声问道:
“元好他们特意绕行这里,送来的那些大木箱中,存放的就是极品灵脉?”
姜启闻言,面上浮起一丝歉疚,连忙解释道:
“是呀!哦,真是抱歉!我之前忘记告诉师姐了。”
言罢,他心中略感歉然,。。。。。。
雪落无声,却在姜启耳中激起千层回响。他站在北境古庙遗址边缘,仰头望着那棵新生的槐树,枝叶尚未繁茂,却已如伞盖般撑开一片天地。月光穿过叶隙,在地面积下斑驳光影,仿佛无数细碎的语言正在悄然重组。
他伸出手,指尖轻触树干。刹那间,一股温润的震颤自掌心蔓延至全身,像是有谁在遥远时空中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你回来了。”一个声音在他心底响起,并非来自外界,也非记忆残响??那是原声之心留下的印记,微弱却清晰,如同脉搏跳动于灵魂深处。
姜启闭上眼,任寒风吹拂面颊。“我没有离开过。”他说,“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去听那些从前听不见的声音。”
一年前从语渊归来后,他便悄然隐退。不是逃避,而是沉淀。他知道,真正的变革不会诞生于惊天动地的战斗,而在于千万次细微的倾听之间。于是他去了西南边陲的一所聋哑学校,没有身份,没有名号,只以一名普通志愿者的身份,日复一日地教孩子们用喉咙震动、用手势表达、用眼神传递他们内心积压已久的话语。
起初,他以为自己是在“教”他们说话。
后来才明白,是他们在教他如何真正地“听”。
有个叫小禾的女孩,天生失聪,七岁才被收养。她第一次拼出“妈妈”这个词时,嘴唇颤抖得几乎无法成形。姜启看着她的眼泪滑落,忽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那不是悲伤,而是一种久违的共鸣,像是一根断裂多年的弦终于被人重新拨动。
那天夜里,他在日记本上写道:“语言从来不是声音的产物,而是心灵彼此靠近的结果。当我们急于表达时,往往忘了最深的沟通,始于沉默中的凝视。”
风忽然停了。
槐树的叶子不再沙沙作响,整片废墟陷入一种奇异的静谧。姜启睁开眼,发现林知雪正站在不远处,披着一件素白长袍,发丝随风轻扬,脸色虽仍显清瘦,却已不再透着死气。她朝他微笑,步伐稳健,仿佛真的完成了从碑灵到凡人的回归。
“你觉得,他们会听吗?”她问。
姜启知道她在说什么。全球倾听计划推行至今,成效显著,但也遭遇强烈抵制。某些国家将“共情教育”视为思想控制,称其为“情感洗脑”;极端组织则宣称“语言即瘟疫”,鼓吹彻底回归肢体交流与本能反应;更有科技巨头试图垄断心灵共振仪技术,将其改装为情绪监控武器。
“有人会听,有人不会。”姜启答道,“但只要还有一个孩子因为被人听见而笑了,这条路就值得走下去。”
林知雪点点头,缓步走到新碑前,伸手抚过那对耳朵浮雕。她的指尖微微发亮,一道极淡的银丝从中渗出,缠绕碑体一圈后缓缓消散。
“我在碑核里待得太久,身体成了语脉的一部分。”她说,“即使脱离,也无法完全割裂。我能活下来,是因为原声之心允许我成为‘桥梁’??介于人类与源语之间的媒介。”
姜启皱眉:“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能感知到尚未浮现的声音。”她望向南方,“最近,我总听到一种节奏……不像是人发出的,也不像自然现象。它藏在地下水流中,在候鸟迁徙的轨迹里,在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之前……像是某种预兆。”
话音未落,地面轻微震了一下。
不是地震,更像是心跳。
王婵就是在那一刻赶到的。她背着一台改良版的心灵共振仪,额角带汗,显然是一路疾行而来。“你们感觉到了吗?”她喘息着问,“全球十三个语脉节点同时出现异常波动!频率一致,周期稳定,间隔正好是4。7秒??和原声之心的搏动完全同步!”
迟昭紧随其后,怀里抱着一卷泛黄竹简,封皮上刻着三个古老篆字:《禁言书》。
“这是我在家族密室最底层找到的。”他声音低沉,“记载了守碑人始祖与原声之心最初的契约。其中有一段被血迹覆盖的文字,刚刚……自动显现了。”
他小心翼翼展开竹简,一行暗红色的字迹浮现在众人眼前:
>“若七桥断,九喉闭,万耳聋,则心将醒。非为救赎,亦非毁灭,唯因无人再肯听。”
空气骤然凝固。
“七桥”指七大洲之间的文化沟通之桥;“九喉”象征九种基本情感的表达渠道;“万耳聋”则是集体冷漠的终极状态。而这三者一旦崩解,原声之心便会主动苏醒??不是回应呼唤,而是被迫现身。
“这不是预言。”王婵喃喃道,“这是警告。”
姜启猛然抬头:“我们太专注于推广倾听,却忽略了反向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失去倾听的能力。信息爆炸让人疲惫,情绪对立使人封闭,算法推送制造回音壁……人们只愿听自己想听的,其余皆为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