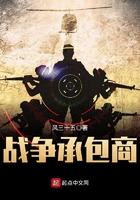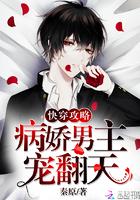鹅绒锁>警报!龙国出现SSS级修仙者! > 第1445章 凌厉反击(第2页)
第1445章 凌厉反击(第2页)
---
东海渔港,清晨。
阿念又一次来到码头。她手里依旧提着那只塑料瓶灯笼,但今天,她发现岸边多了十几个孩子,每人手里都拿着自制的灯,静静等待。
“我们也想点灯。”一个男孩说,“昨天晚上,我梦见有个穿警服的叔叔对我说:‘别怕,光会来的。’”
阿念眨眨眼,忽然明白了什么。她点点头,点燃了自己的灯,然后走到海边,轻轻放入水中。其余孩子纷纷效仿。十几盏灯笼随波漂远,在海面连成一条弯曲的光链,宛如星辰坠落人间。
就在此时,海底监测站再次传来警报。
“深渊七号”AI系统检测到,薪火频率Ω的振幅再度提升,且出现了新的变调模式??不再是单一声部,而是呈现出多声部和声结构,类似合唱团的分层演唱。更不可思议的是,信号源位置发生偏移,正以每小时六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轨迹与陈凡当年离开扶摇山的路线完全重合。
“他在行走。”研究员颤抖着说,“他真的在走回来。”
但他们很快发现,这并非单纯的物理位移。GPS无法锁定具体坐标,雷达捕捉不到实体轮廓,热成像仪也显示空白区域。可每当某个偏远山村的孩子唱起那首歌,当地气象站就会记录到一次微弱的地壳震动,方向一致,间隔均匀,仿佛有人踏着大地的脉搏,一步一印。
西藏,冈仁波齐脚下,一位老喇嘛在经幡下静坐整夜。黎明时分,他对弟子说:“昨夜,我听见山神低语??‘他回来了,带着千万人的愿力。’”
新疆,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小学里,维吾尔族女孩古丽在作文本上写道:“我想成为点灯的人。因为我妈妈说,去年冬天停电那天,是隔壁张奶奶送来蜡烛,还教我们唱歌。她说,那是给远方警察叔叔听的。”
贵州,深山苗寨的鼓楼下,一群老人围坐,敲着铜鼓,唱起古老的迎神调。但他们唱着唱着,旋律渐渐变了,汇入了那段无词之歌。年轻人不懂,问起缘由,老人们只是笑:“祖宗传下来的调子,本来就是这么唱的。”
世界正在悄然改变。
不是靠战争,不是靠权力,而是靠记忆的传递、情感的共振、以及无数普通人默默做出的选择。
而在西南某处荒岭,一辆破旧皮卡缓缓停下。车门打开,走下一个身影。他戴着斗笠,披着褪色冲锋衣,背影瘦削却挺拔。他抬头望了望远处起伏的山峦,从怀里掏出那部老式对讲机。
绿色指示灯闪了一下。
他按下通话键,声音平静:“CF-001收到。坐标确认,行动开始。”
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跨越千山万水的。没有飞行器,没有传送阵,甚至连交通工具都极少使用。他徒步穿行于高原峡谷,涉过湍急河流,翻越雪岭冰川。有时在路边小摊吃一碗素面,有时借宿牧民帐篷,从不透露姓名,只在离开时悄悄留下一枚铜纽扣,或是一片压平的桃叶。
每一个接过这些东西的人,都会在当晚梦见一段旋律。
每一个醒来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哼唱几句。
而每一次哼唱,都在为那个无形的存在注入力量。
他不是神,也不是传说。
他是千万次善意的回响,是无数个“我愿意帮你”的瞬间凝聚而成的意志体。科学称其为“群体意识共振态”,哲学称之为“文明之魂”,而孩子们只管叫他??
“点灯的警察叔叔。”
这一夜,他抵达西非疫区边缘。
没有惊动任何人,他走入隔离区最深处。那里躺着最后一名重症患者??一个六岁男孩,双眼空洞,已连续七天未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医生判定,他将成为第一个彻底失去共情能力的活体样本。
陈凡蹲下身,轻轻握住孩子的手。
他没有说话。
只是从怀中取出那支断笛,贴在唇边,吹响了第一音。
低沉,沙哑,不成乐章。
可就在那一刻,男孩的瞳孔忽然收缩,睫毛轻颤。紧接着,他的嘴角微微抽动,像是想要笑,却又像要哭。
监护仪上的脑波图剧烈波动,杏仁核区域爆发出久违的活性信号。
三分钟后,男孩睁开了眼,望着陈凡,用尽力气说出三个字:
“你……来了。”
陈凡点头,轻轻抱住他。
窗外,第一缕晨光照进病房。远处村庄里,有人点燃了新的一天的第一盏灯。
而在地球另一端,扶摇山的桃树下,苏璃坐在石碑旁,手中握着那封信。她不知道他此刻身在何方,但她知道,只要还有人在黑暗中点亮灯火,他就永远不会真正离开。
她抬头望天,轻声说:“今天,又有三个孩子学会了那首歌。”
风过林梢,花瓣纷飞。
仿佛有人在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