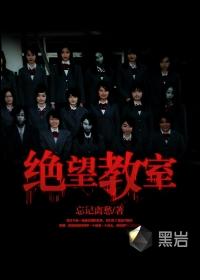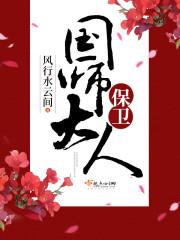鹅绒锁>九龙夺嫡,我真不想当太子 > 第三百五十八章 用一个圣人打另外一个圣人(第3页)
第三百五十八章 用一个圣人打另外一个圣人(第3页)
他已不再是当初青涩太子,而是历经风雨的君王。鬓角微霜,眼神坚毅,身上带着长途奔波的疲惫与思念。
“您走时只留八字,害得整个朝廷以为您遭不测。”赵景珩抬头,“这些年,民间谣言四起,有人说您被西域妖僧蛊惑,有人说您复辟前朝,更有甚者,声称您才是真龙天子,要率军迎您回京登基!”
赵承渊放下扫帚,扶起儿子:“那些话,你也信?”
“不信。”赵景珩摇头,“但我知道,只要您还在,我就不会迷失方向。新政推行遇阻时,我常想:若是父皇在,他会如何做?每思及此,便有了勇气。”
赵承渊拍拍他肩头:“你能这样想,说明我没白退。”
父子二人围炉夜话。赵景珩带来最新奏报:北疆归附三部,南方海运开通,科举新增“廉政策”,监察御史可直谏天子;更有意思的是,今年殿试状元竟是一名女子,化名赴考,文章惊动四海,揭榜方知真相。赵景珩力排众议,授其翰林编修之职,开创女子入仕先河。
“您若看到她的文章,定会欣慰。”赵景珩笑道,“她说:‘天下之治,在选贤与能,岂分男女?’”
赵承渊大笑:“好!这才是真正的贞观气象。”
次日,他随太子启程返京。一路所见,皆是升平景象:道路修整,驿站林立,乡塾遍设,茶肆酒楼重现繁华。沿途百姓不知其身份,只觉这位白发老者慈眉善目,便争相送上热汤干粮。
回到西山别苑,谢无咎与游璧早已等候多时。三人对坐饮酒,一如当年。
“你这一走,差点让我们以为你真成了神仙。”谢无咎叹道。
“我不是神仙。”赵承渊举杯,“我只是个终于明白自己是谁的人。”
晚宴过后,他独自登上后山,望向慈恩寺方向。九盏长明灯依旧明亮,第九盏光芒最盛,仿佛穿透岁月,照亮过往所有黑暗。
他轻声呢喃:“七哥,母妃,柳嬷嬷……我都记得。我没有辜负你们。”
数月后,一部匿名撰写的《前朝遗事考》悄然流传于士林。书中详述永昌年间宫廷秘辛,虽未点名道姓,但明眼人皆知所指何人。朝廷未加禁止,反而默许传播。渐渐地,民间开始议论那段被掩盖的岁月,有人叹息,有人愤怒,也有人反思。
赵景珩下诏设立“史鉴馆”,召集天下学者整理前朝史料,允许自由辩论,唯有一条禁令:不得煽动复仇,不得鼓吹叛乱。
十年后,一本名为《贞观政要》的新书问世,作者署名“渊叟”。书中总结治国之道,强调“去私心、存公义、重民生、抑特权”,被誉为新时代的治国宝典。皇帝亲自作序,称其“字字如金,光照千秋”。
而那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太上皇,终其一生未再涉足权力中心。每年冬至,他仍会前往玄冰台旧址,点燃一炷香,祭奠所有死于夺嫡之祸的兄弟。
直到某年深秋,他病卧床榻,气息微弱。临终前,他召来赵景珩,握住他的手,留下最后一句话:
“记住……真正的帝王,不是坐在龙椅上的人,而是能让更多人挺直腰杆活下去的人。”
言罢,含笑而逝,享年七十有三。
举国哀悼,罢朝三日。百姓自发焚香祭拜,孩童传唱那首旧童谣:
>“九龙争鼎血成河,
>一朝风雨洗山河。
>不见龙袍金螭印,
>只闻慈恩诵经多。
>谁言帝王无情义?
>却把江山换黎歌。
>若问圣君何处觅?
>松涛深处是渊庐。”
多年后,有史官修撰《新史?列传》,为其立传,题曰:
>**“太上皇赵承渊,少历艰危,中兴社稷,功成身退,归隐林泉。不以权位自矜,不以仇怨报复,化戾气为祥和,转杀伐为教化。虽无帝号之实,实具圣王之德。故君子谓:承渊者,承天下之渊也。”**
而在西域forgottentemple的密室中,那块血帕静静躺在金棺之内,半朵莲花依旧鲜艳如初。
每当风雪之夜,寺中钟声悠扬,仿佛仍在诉说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赵昭衡之子,赵承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