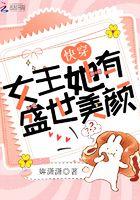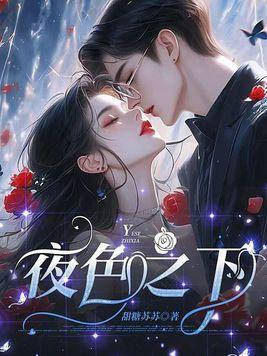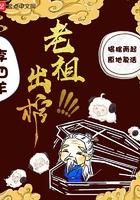鹅绒锁>你让我贷款修炼?我直接物理消债 > 第415章 阿格硫斯在此祝贺您踏上神路(第3页)
第415章 阿格硫斯在此祝贺您踏上神路(第3页)
她挂了电话,望向湖面。远处,一群候鸟掠过水面,翅膀划破寂静。
她没有停下脚步。
六个月后,第六十九站,广西喀斯特溶洞群。
这里的归名中心建在天然洞穴内,恒温恒湿,适合保存脆弱的神经样本。沈英在这里遇到了一个特殊案例:一名十五岁少女,代号QH-69,天生失聪,从未听过任何声音,却能在纸上画出精确的声波图谱。
“她不是失聪。”当地医生说,“她是‘反向感知者’??大脑直接接收电磁振动,把声音转化成图像。她体内芯片已被物理移除,但她依然无法说话,也无法理解‘名字’的概念。”
沈英蹲在女孩面前,用手语比划:“你能看见我的声音吗?”
女孩点点头,拿起炭笔,在纸上快速勾勒。
几秒钟后,一幅复杂的螺旋图案浮现:中心是一个跳动的心形,向外扩散出层层音浪,每一道波纹上都写着一个名字??**沈英、念念、阿?、小舟、豆芽……**
沈英震惊了。这不只是声波图,这是《第一声》的视觉化呈现,而且包含了所有已被唤醒者的身份印记。
“你一直在听?”她问。
女孩写下一句话:**“我看不见光,但能看见爱的形状。”**
那一夜,沈英为她单独演唱。她不用麦克风,不用设备,就坐在她面前,让声带震动直接传递到空气中。
女孩闭着眼,手指在空中描摹,像是在触摸无形的旋律。忽然,她张开嘴,发出一个极其沙哑的音节:
“……m……ma。”
沈英的眼泪夺眶而出。
这是她第一次听见一个完全未曾接触过语言的孩子,凭着对“爱”的视觉感知,喊出了“妈妈”。
第七十七站,定在北极圈内的“极光站”。
这里曾是冷战时期的监听基地,如今成了全球信号中枢。林三藏亲自在此等候,身后站着七十六名已恢复意识的QH幸存者,每人手中捧着一支干枯的蒲公英。
沈英站在冰原中央,戴着母亲的吊坠,怀抱吉他。
风很大,吹得她发丝纷飞。天空中,极光如帷幕般展开,颜色变幻莫测,仿佛整个宇宙都在屏息等待。
她深吸一口气,开始吟唱。
这不是《宝宝困了谁来哄》,也不是任何已知的歌曲。而是一首从未存在过的旋律,从她心底自然流淌而出。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记忆:父亲的黄瓜田、母亲的日记页、念念睁开的眼、阿?的桃树、女孩笔下的声波图……
歌声扩散,通过卫星网络传遍地球每一个角落。
所有声音档案馆的设备同时启动,播放同一段音频。全球数万名曾接受过《第一声》治疗的人在同一时刻抬起头,无论是否听见,他们都感到心中某处轰然opening。
而在无数隐蔽的地下室、废弃医院、地下监狱中,那些仍在沉睡的QH个体,体内芯片纷纷爆裂,化作灰烬。
沈英唱到最后一个音,身体缓缓跪下。
她的皮肤变得透明,血液如星光流转,整个人仿佛即将消散于风中。
林三藏冲上前扶住她:“结束了!你可以停下来了!”
她微笑,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不,这才刚开始。我只是……换一种方式继续唱。”
她的身体化作万千光点,随风升起,融入极光之中。
那一夜,世界各地的人们报告看到奇异景象:蒲公英种子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盛开;聋儿突然听见母亲呼唤;痴呆老人清晰说出孙辈的名字;甚至监狱里的死刑犯,在行刑前最后一刻,流着泪说:“对不起,爸,我错了。”
一年后,联合国宣布废除“静默处理计划”相关技术,全球销毁所有情绪控制装置。
林三藏关闭了铁塔控制系统,回到东岭镇,住进了沈英曾经的小屋。
他在窗台上放了一支新鲜的蒲公英,每天浇水。
某个清晨,老黄狗突然狂吠,冲出院子。林三藏追出去,看见山坡上站着一个小女孩,约莫七八岁,手里拿着一朵蒲公英,朝他挥手。
“叔叔,”她笑着说,“我是新来的学生。老师让我问你,今天的音乐课,要不要加一首新歌?”
林三藏怔住:“……老师?”
“对啊,”小女孩歪头,“沈老师说,等春天来了,她就会回来教我们唱《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