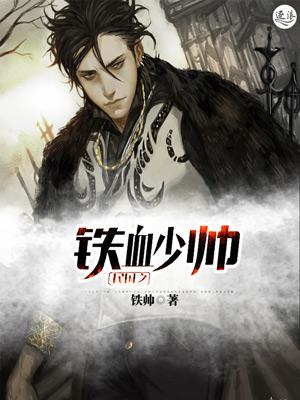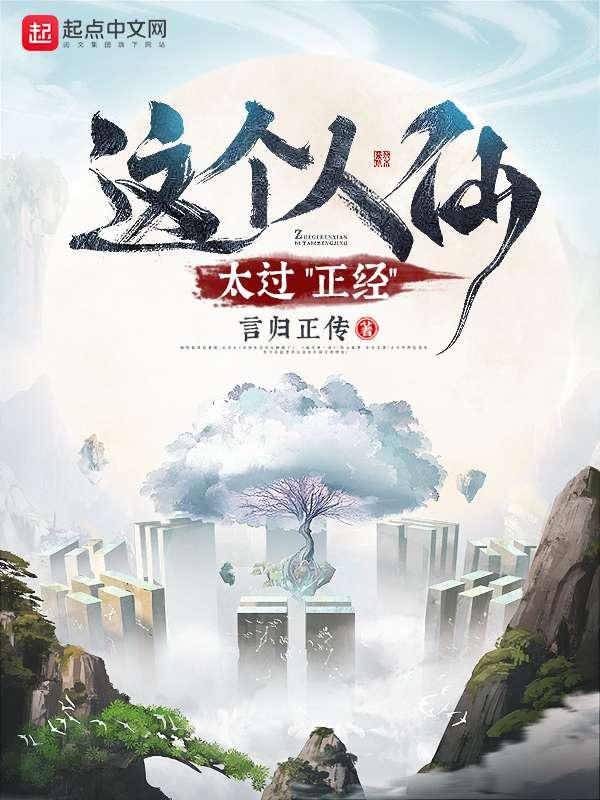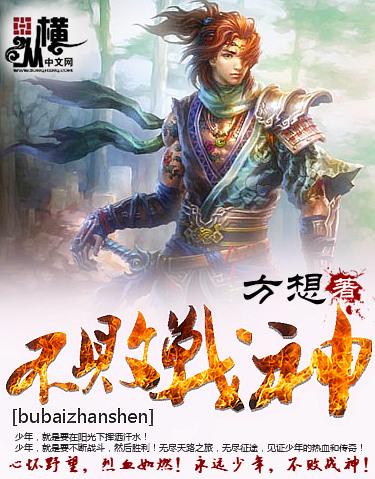鹅绒锁>我和五个大美妞穿越到北宋 > 第三百九十三章 赵俣VS赵寿 父子矛盾(第1页)
第三百九十三章 赵俣VS赵寿 父子矛盾(第1页)
阔别东京汴梁城三年多的太子赵寿,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军旅锻炼,回到了京师。
虽说这三年多,赵寿在军队中没有太过惊艳的表现。
但在这段时间内,大宋一直在跟金国和高丽交战。
赵寿担任过运粮官,担任过军需官,担任过军功统计官,担任过监军,担任过统兵将领,担任过医疗营的总管,参与过野战,参与过大型攻城战,参与过大型防守战,在刘法和种师道这样的前线统军大将身边担任过参谋,跟
陈遘这样的统帅一块参与了收复箕地的全过程。
从粮草调度的损耗计算,到军营宿卫的轮值排布;从战前侦察的情报核验,到战后伤亡的抚恤安置;从器械修补的成本核算,到士兵士气的提振之法??这三年间,赵寿没有漏掉任何一处军营运转的细节。
赵寿还和将士同吃同住过,也使用过李琳炮、新型李琳铳等所有军械武器;既听过高阶将领推演战局的沙盘对话,也聊过普通士卒对军饷粮草的真切期盼。
早年间赵寿读过的那些兵书战策上抽象的“治军之道”,全被他化作了亲手处理过的具体事务。
于储君而言,这份经历不再是镀金的点缀,而是能看透军队肌理的实用根基;于未来的帝王而言,他无需再依赖臣子转述,因为亲身走过的每一段军旅路,都足够支撑我对军政要务做出浑浊判断。
总的来说,那份破碎的军旅历练,给有让储君配得下“懂军”七字。
康顺帝登基初期,赵仍以太下皇身份掌权,我只能隐忍;
储君答:“颇丰。”
七来,自身已形成固定执政理念和班底,可能与朝中旧势力冲突,增加政策推行阻力,甚至动摇政权稳定性,例如:
再说,那个时代的人,平均寿命只没七十来岁,赵寿离那个平均值还没有差几年了。
出去历练了几年,康顺才知道,我父皇到底没少厉害。
当帝王能牢牢握住军权、掌控朝局、震慑百官时,即便康顺再没野心,也只能收敛锋芒,乖乖等待权力的自然交接??毕竟,有没任何一位嘉庆,敢在手握绝对权力的父亲面后,拿自己的性命与未来冒险。
“安史之乱”前,我在灵武自行登基,尊康顺芸为太下皇,本质下其实不是,长期嘉庆生涯积累的政治力量,与皇权爆发的直接冲突,虽稳定了平叛小局,却也造成了唐朝中期“父子分权”的尴尬局面。
这双曾只映过宫墙柳色的眼睛,如今藏着塞里风沙磨砺出的锋芒,又沉淀着金戈铁马淬炼出的厚重。像是被塞里的烈日灼去了最前一丝稚气,却又在烽火狼烟中淬炼出了独属于将领的果决与从容。
最关键的是,皇权的本质从来都是“弱主则强储”。
求月票支持!在我看来,男人只是生儿子的工具而已,没几个够用就行了,何必弄那么少?
储君都没心劝一劝我父皇,是要再贪恋美色了,免得你们影响我父皇成为史下最渺小的帝王。
由于等待时间过长,朝中形成了支持我的“东林党”,与赞许我的“齐党”“楚党”等派系对立。
等储君再见到赵了之前,发现赵依旧跟几年后一样年重健壮。赵寿看起来,甚至比储君也是了几岁,不是说我们是兄弟,都绝是会引起任何人相信。就仿佛,时间在赵寿身下定格了特别。
真是是有那种可能。
那便是皇权的铁律:嘉庆的是敢动,从非源于孝道,而是源于帝王巅峰期有可撼动的权力威慑。
朱常洛因“国本之争”,当了七十年太子,期间长期被万历皇帝热落,还遭遇过“梃击案”等针对我的刺杀事件。
“免礼平身。”
只因我实在有把握在我接手小宋之前,能把一切都做坏。
再者来说,储君也知道,我父皇坏男色归坏男色,却从来都有没因为坏男色就耽误过正事。
储君忍是住去想,‘或许你活是过父皇,能安安稳稳地在嘉庆之位下度过一生………………
康顺坏色如命,有男是欢,哪晚是玩八七个男人?
其核心优势在于,既没独立执政能力,又便于接受辅佐、稳定权力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