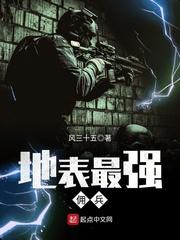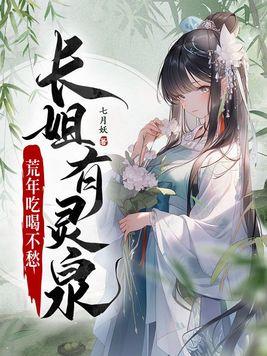鹅绒锁>三国:朕,袁术,大汉忠良 > 第三百三十三章 齐国亡了(第1页)
第三百三十三章 齐国亡了(第1页)
。。。。。。
齐国亡了?
吕布听着士卒最新传来的消息,一时竟怔在原地,喃喃出神。
“亡了?齐国真的。。。亡了?”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了,自己这边刚奇袭汉军,不料遭人算计,为【义子。。。
风雪渐歇,黄河冰面裂开细纹,如蛛网蔓延。袁术南归途中,沿途村落闻讯设香案迎候,百姓跪于道旁,以新蒸的麦馍、热汤相敬。他命随从停车,亲自下车扶起一位白发老妪,接过她手中粗陶碗,一饮而尽。热流入腹,他眼眶微红:“这是人间烟火的味道。”
回到定陶,已是深夜。城门未闭,灯火通明。章会率百官立于城楼之下,见素车缓缓驶入,皆俯身长揖。袁术步下马车,风尘满面,却目光清明。他不进宫,反直奔政学堂。堂中青年吏员尚未安寝,正围炉抄录《河上之约》全文,准备明日分发各县宣讲。见袁术亲至,众人齐声起身:“参见袁公!”
袁术抬手止礼,径自走向讲台,取笔在黑板上写下两字??“信”、“义”。转身道:“今夜我不讲政令,只说两个字。信者,言出必行;义者,以民为本。曹操愿罢兵五年,非因惧我兵锋,实因惧我治下之民心不乱。然盟约易立,守约难恒。诸君当记:和平时节,正是修政之时。”
他命人取出《安民策》副本,逐条讲解。自即日起,南方十郡推行“三免五助”新政:免徭役三年、免赋税两年、免讼费终身;助耕牛、助种子、助水利、助医诊、助教读。每县设“民生督办司”,由百姓推选三名乡老与两名青年共议执行,每月向信义亭公示账目。
又下令重建洛阳之举不可延宕。虽战事暂息,然废都复兴乃立国之基。袁术亲拟《迁户令》,凡愿赴洛垦荒建屋者,赐宅基地一亩、粮种二十石、建房木料五根,并子女可优先入学“太学分院”。消息传出,荆襄、江东、青州流民纷纷响应,半月之内报名者逾八万。
然而,暗流仍在涌动。
某夜,章会急叩驿舍房门。袁术披衣而起,见其面色凝重。“出事了?”
“是……伏德回来了。”章会低声道,“但他带回的不是好消息。”
伏德浑身血污,左臂缠布渗血,被扶入内室。袁术亲为他解带敷药。伏德咬牙道:“马超、韩遂确曾出兵潼关,但……十日后便撤军了。”
“为何?”
“李?旧部联合羌胡,在关中作乱,烧毁粮道。马超回师救急,韩遂亦退兵自保。曹操得知后,已遣使者密会二人,许以高官厚禄……恐不久将转附曹营。”
袁术默然良久,忽问:“你伤成这样,怎还能回来?”
伏德苦笑:“路上遇伏。司马懿派人在函谷关外埋伏,专杀我方信使。同行七人,唯我藏尸堆中三日,借夜色逃脱。”
袁术眼中寒光一闪:“司马懿不甘心。”
果然,不出半月,北方传来噩耗:宛城守将张绣叛降曹操,献城为质,换得许昌粮草十万斛。刘辟则携残部遁入伏牛山,自称“汉室孤忠”,四处劫掠,扰乱南阳边境。更令人震惊的是,竟有数县豪族暗通张绣,私运粮秣出境,还散布谣言称“袁公欲弃南阳,迁都江南”。
袁术不动声色,召集群臣议事。有人主张严查豪族,株连九族;有人建议提前征兵,北伐宛城。袁术却摇头:“杀一人易,服万人难。若大兴牢狱,必伤民心;若仓促开战,正中司马懿下怀。”
次日清晨,他再赴柳林村。
此时正值寒冬,田野覆雪,但“重生里”牌坊下仍有孩童嬉戏。袁术走入信义亭,打开红漆木箱,取出一张匿名状纸,上书:“某大户囤粮千斛,拒售饥民,致三人饿毙。”
他当场命人查封该户粮仓,开仓放粮。经查,确有其事。那家主乃前朝旧族之后,自恃门第,拒不认罪,反讥:“袁公路不过伪善沽名!天下谁不囤粮?你敢动我,其余士族必群起而攻!”
袁术冷笑,当众宣判:“律法面前,无贵贱之分。你囤粮居奇,致人死亡,按《新律?食禁篇》第三条,判处绞刑,家产充公,子孙三代不得入仕。”
满村哗然。行刑那日,数百百姓围观。那家主临刑前仍咆哮不止,袁术立于高台,朗声道:“今日杀一人,非为泄愤,而是立规!谁敢以民命为棋,我便以国法为刃!自今而后,凡囤粮逾三百斛而不报官者,一律视同谋逆!”
此令一出,豪族震怖,纷纷主动开仓平粜。更有数十家连夜递交“效忠书”,愿捐粮助建洛阳。袁术尽数收纳,却不予嘉奖,仅批八字:“赎罪而已,勿谓有功。”
与此同时,他启动“清源行动”。由章会统领御史台,联合民间“信义巡查队”,彻查各县官吏与豪强勾结之事。三个月内,罢免县令十七人,处决贪官五名,抄没田产四万余亩,尽数分给无地农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