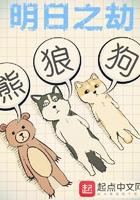鹅绒锁>华娱从洪世贤开始 > 第601章 大哥你是了解我的(第3页)
第601章 大哥你是了解我的(第3页)
全场寂静数秒,随即爆发出热烈掌声。
这段视频迅速传播,成为网络热梗:“你说电影太沉重?那是因为你活得足够轻。”
风波未平,新的机遇已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来邀请,《普通人》将作为“全球人文影像代表作”参展巴黎青年电影节。组委会特别注明:“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影片本身,更是它引发的社会运动。”
出发前夜,全体主创再聚首。地点仍是那所南方小镇的祠堂。月光如水,洒在石阶上。大家席地而坐,喝着自酿的米酒,聊着过去,也谈未来。
许兰忽然提起:“其实我一直有个秘密没说。我妈临终前,给我写了封信。她说,‘兰兰,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不是没成名,是没有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被看见。如果你有一天能站在光里,请一定记得拉一把还在暗处的姐妹。’”
她顿了顿,望向周小雨:“所以当我看到你收集的那些故事时,我就知道,这不只是你的电影,是我们所有人的救赎。”
周小雨眼眶湿润,点头:“我爸爸最后流的那滴泪,不是因为片子好看,是因为他终于听见了??有人替他说出了那句憋了一辈子的话:‘我不是失败者,我只是没机会。’”
林浩然举起酒杯:“敬所有未曾发声的灵魂,敬所有敢于开口的勇者,敬所有愿意倾听的耳朵。”
众人齐声应和:“干杯。”
翌日清晨,他们踏上旅程。飞机起飞时,林浩然望着窗外云海翻涌,想起十年前那个蜷缩在出租屋写剧本的自己。那时他以为成功是拿奖、是成名、是万人追捧。如今他终于明白,真正的荣耀,是让一个修车工打磨的木剑出现在国际影展的展映名单上;是让一个山区女孩的朗诵声穿越千山万水,抵达巴黎的夜空。
抵达巴黎当晚,露天放映会在塞纳河畔举行。数百名留学生与当地华人自发前来,不少人举着中文标语:“我们都是普通人。”当电影结尾孩子们齐声朗诵那段台词时,现场许多人跟着一起念:
>“我是普通人,我没有光环,没有热搜,没有百万粉丝。
>我说的话不会上头条,我的眼泪不会被剪成短视频。
>可我还是想说??
>我存在,我呼吸,我疼痛,我欢喜。
>这就够了。”
声音用中文、法语、英语交替响起,最终融为一体。
一位法国记者采访林浩然:“您认为这部电影为何能在不同文化间引发共鸣?”
他想了想,答道:“因为痛苦不分国界,渴望被听见的心也是如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普通人’,他们或许语言不同,但眼神一样明亮??那是不肯熄灭的光。”
归国后,《普通人》系列正式启动第二阶段。除了影视化项目,还衍生出线下剧场巡演、社区口述史工作坊、青少年表达训练营等多个分支。教育部将其纳入“美育创新试点案例”,多地学校引入“普通人课程包”,引导学生采访长辈、记录家族记忆。
而最让林浩然欣慰的是,许兰决定成立“母亲基金”,专项资助基层女性艺术工作者重返舞台。首位受助者是一位五十岁的乡村豫剧演员,因家庭变故中断演出二十余年。复出首演那天,她在台上唱完一折《穆桂英挂帅》,跪地叩首:“我不是为了成名,只是为了证明,女人到了五十岁,也能为自己活一次。”
台下,许兰泪流满面。
某个雨后的傍晚,林浩然再次回到最初构思剧本的房间。桌上那支旧钢笔还在,旁边多了厚厚一摞信。有小学生写的观后感,歪歪扭扭却真诚;有老兵回忆战争年代战友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还有一位监狱服刑人员来信:“我看了电影,开始写忏悔录。也许我无法弥补过错,但至少,我想让受害者家属知道,我听见了他们的痛。”
他拿起笔,在新稿纸上写下第一行字:
>“所谓英雄,不过是普通人挺身而出的那一瞬间。”
然后停顿了一下,又添了一句:
>“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让那一瞬,被世界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