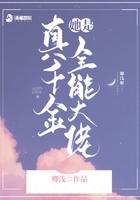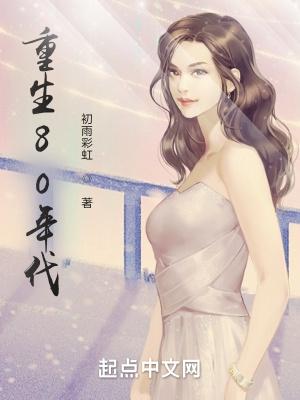鹅绒锁>谁说这顶流癫!这顶流太棒了! > 第406章 爆开团秒跟的池野方(第2页)
第406章 爆开团秒跟的池野方(第2页)
前奏响起,缓慢而深沉,带着北欧民谣特有的苍凉感。他开始唱:
>"Youwerethevoicenooneheard,
>Thesongstuckinabrokenchord。
>Youworesilencelikeacoattootight,
>Andcalleditstrengththroughsleeplessnights。
>ButIsawyou。
>Iheardyou。
>AndIcarriedyourmelodyacrosssevenwintersandthreeseas。。。"
(你是无人听见的声音,
是卡在断裂和弦里的歌。
你把沉默穿成一件太紧的外套,
却称之为坚强,熬过无数无眠之夜。
但我看见了你。
我听见了你。
我把你的旋律,带过了七个冬天和三片海……)
歌声落下时,整个屋子陷入了长久的静默。一位白发老太太缓缓起身,用手帕擦着眼角,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这是我孙子最喜欢的歌手去世前写的诗……你怎么会唱出来?”
池野怔住:“您能念一遍原文吗?”
她颤抖着掏出一张泛黄的纸条,读出几句冰岛语。池野闭上眼,片刻后睁开:“这不是我写的歌词……但它们在我心里,已经存在很久了。”
那一晚,他留在了这家小小的LiveHouse,与本地音乐人即兴合作,用中文、英文、俄语、日语甚至几句生涩的冰岛语拼凑出一首名为《无名者之歌》的作品。录音被上传至社交平台后,二十四小时内播放量突破千万,评论区涌来无数故事:
“我在叙利亚难民营教孩子画画,他们从未听过你的名字,但当我播放那段音频,一个十岁的男孩说:‘这声音像风穿过废墟的样子。’”
“我是深圳电子厂流水线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昨晚我戴着耳机听你唱《冬日私语》,第一次觉得,原来我也值得被温柔对待。”
“我母亲阿尔茨海默症晚期,已经不认识我了。但她昨天听到你在莫斯科的演出视频,突然哼起了年轻时学过的《喀秋莎》。医生说这是罕见的情感唤醒现象。”
池野一条条看完,坐在床沿许久未动。窗外,晨光初现,照在积雪的屋顶上,反射出柔和的金色。
三天后,他启程回国。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时,已是傍晚。接机口没有粉丝围堵,没有媒体长枪短炮,只有陶城和任颖站在出口处,手里举着一块手写牌子,上面画着一朵雪花,写着:“欢迎回家,考古学家。”
四人聚餐时,陶城问他:“下一步真要办学校?钱呢?政策呢?师资呢?你知道国内这类机构活不过两年的比比皆是。”
池野点头:“我知道。所以我打算先从线上做起,搭建一个全球音乐共创平台,让不同国家的孩子远程合作写歌。等模式跑通,再落地实体校区。第一所,我想建在云南山区,那里有个听障儿童合唱团,去年靠手语演绎《茉莉花》拿了国际奖。”
任颖看着他:“你变了。”
“是成熟了。”陶城接道,“以前他是顶流里的异类,现在他是异类里的顶流。”
饭后,三人陪他去了北京郊区的老屋??那间他曾与林昭合租的小平房。如今已被房东改造成民宿,但池野还是拿到了钥匙,进去看了看。
墙皮剥落,地板吱呀作响,厨房角落堆着旧锅碗瓢盆。他走到卧室,掀开床底的木板,取出一个铁盒。里面是一叠泛黄的乐谱草稿、几封未寄出的信,还有一张两人合影:年轻的池野和林昭站在天台上,背后是整座城市的灯火,他们笑着,手里举着两瓶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