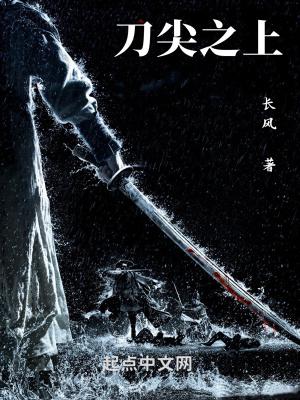鹅绒锁>朕与将军解战袍gb > 长安客4(第2页)
长安客4(第2页)
五月芳菲尽,宫中因多了一批女官,格外忙碌起来。柳芳歌正神色威严地吩咐着什么,忽闻外头传来打骂声:
“让我进去!里头是我阿姐,我凭什么不能进?!”
外头的姑姑为难地拦他:“公子,这里算是内宫,您一介外男无召入内,于礼法不合啊!”
“我不管!哪里的礼法规定了我不能见自己的姐姐?!”
………
柳芳歌蹙了蹙眉,推门出去,声音冷静:“什么事?”
柳扶洲看见她来,好似乱撞的雀儿瞧见了主人,眼睛都亮了起来,巴巴地看着她:“阿姐!这老货好生木讷,我是你弟弟,怎地连来探望你都不许?”
柳芳歌的眉头依然蹙着,她低声喝道:“扶洲,不许胡言乱语!这里是皇宫,休得撒野,快给姑姑赔罪。”
柳扶洲嘟了嘴,很不满地瞪了姑姑一眼,碍于柳芳歌,只好把火气压下去,他偷眼瞥了一眼柳芳歌,道:“可是我好久没见到阿姐了呀。阿姐自从得了官职就不往家里来,我还有件喜事要告诉你呢……”
柳芳歌面色缓和了些,她无奈地叹了口气,柔声道:“好,阿姐马上就来陪你。不过内宫重地,不得擅闯。你听话点,别叫阿姐难做。”
她又转过身,笑着塞给老嬷嬷几块碎银:“家弟自幼顽劣,姑姑莫要放在心上。”
老嬷嬷原本神色僵硬,瞧了银子,面色好看了不少,赔笑道:“柳姑娘说的什么话,使不得、使不得。”
柳扶洲撇了撇嘴,这天不怕地不怕的混世魔王居然真的安静了下来,站在宫门外无所事事地踢小石子。
柳芳歌快刀斩乱麻地处理完事务,把柳扶洲拉到茶楼里。她容颜过于妩媚,走入茶楼时有许多人偷眼看她,被柳扶洲一把将帘子拽上。
柳扶洲笑眼弯弯地看着她:“阿姐,父亲说我马上也要有官职了,你开不开心?”
柳芳歌只是淡淡地看着他,脸上一丝笑意也无。
柳扶洲说着说着,感觉到她的冷淡,有些犹豫地住了嘴。
柳芳歌执壶替他满上一杯茶,推到他跟前:“喝了吧。”
柳扶洲喝了下去,随即又苦得吐了出来,他脸皱了一团,不满道:“阿姐明知我不喜欢苦的!”
柳芳歌眼尾翘了翘,渗出一些笑来,却是冷的,她声音很轻,飘飘渺渺:“我知道扶洲不爱喝苦的,我也不爱喝。可是我喝了十七年。”
有一些茶水洒出来,将她手指烫出一片红,柳扶洲皱了眉要去替她吹吹,被她抬手止住了。柳芳歌望着他,面上无波无澜:“你不爱喝便可以吐出来。我却不能。扶洲,我喝了十七年。”
柳扶洲没见过这样的阿姐,在他的记忆里,阿姐总是温柔的、和善的,小时候他犯了错每每要被责罚,阿姐便跑去喊老主母,给他搬救兵。老主母一来,父亲再大的气也只能压下去,久而久之,倒对他犯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阿姐还会耐心地陪着他玩,给他缝衣服,十岁那年,他野外遇蛇,险些命丧黄泉,也是阿姐为他吸出毒水,冒着瓢泼大雨背着他去求救。阿姐是世界上最好的阿姐。
他无措地问:“那阿姐为什么不能吐出来?”
“因为你呀。”柳芳歌弯起唇,伸出一只葱白的指头点了点他眼前的杯子。
柳扶洲瑟缩了一下,他没搞懂,还想再问,就听见柳芳歌的声音,柔软得像小时候他哭泣时安慰他那样:“因为要给你铺路呀,扶洲。父亲一早打算了要把我嫁给天家,我必须护着你、扶着你、供着你,让你一辈子无忧无虑又愚蠢至极地活下去。”
柳芳歌的眼尾浮出一丝血色,她笑起来,笑得花枝乱颤,好一会儿才抹去眼角笑出来的泪珠:“你在外头为非作歹时,我被关在书房练字,一直练一直练,手上磨出了血泡。只因为太子喜爱书法。”
“太子有一阵子喜爱听琴,于是父亲又让我学琴,八月伏旱天,我在闷热的琴房练了三天三夜的琴,若不能完整地弹出一曲《解语花》便不能出去。后来我昏倒在地,好一阵子才被人发现。”
“太子喜爱什么样的人,父亲便会要我变成什么样。我是一件礼物,随时等着送人。”她好不容易才止住笑,垂下那双好看的眼,不自觉重复了一遍,“随时等着送人。”
从始至终,柳芳歌都语气平缓,听不出什么情绪,柳扶洲却随着她说的话,面色一点点白下去,良久,他干涩地问:“为什么我不知道?”
“父亲怎么会叫你知道呢?”柳芳歌翘了翘唇角,温和地道,“他们都希望你无忧无虑啊。”
她望着手中的茶杯,清波里映出一张娇艳的脸,每一寸肌肤都莹白如雪,每一次微笑都得体雍容。那是她自己,是柳家培养出的尤物。
柳扶洲徒劳地看着她,拼命想要说什么,却说不出来,柳芳歌冷眼看着,突然觉得好没意思。她站起来,轻声道:“扶洲,往后别来找我了。”
那向来飞扬跋扈的少年好似被人打了一闷棍,眼眶迅速地红了,问:“阿姐讨厌我?”
柳芳歌没有给他答复,她只是淡淡看了他一会儿,目光里没有情绪。随后她像是觉得寒冷,拢了拢外袍,兀自转身走了。她脑后繁复的步摇晃啊晃,在柳扶洲眼前晃出一片重影,渐渐地模糊成看不清的雾霭。他抬手一摸,摸到一手冰凉。
“阿姐。”
“阿……姐……”
但是没有人会再笑着应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