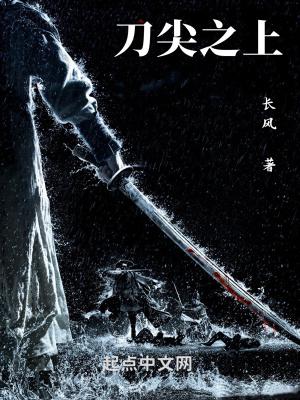鹅绒锁>我早就不喜欢你了,狗皇帝 > 90100(第13页)
90100(第13页)
聘为妻,奔为妾,这是要她再无清誉啊。
像是看懂了她的神色,谢朝宗撑着下巴,看着她认真道:“宁宁,你大可不必忧心,我定不会像是封砚那般三心二意,我将来娶你,后院也只会有你,绝不会再有旁人,可好?”
“一点也不好!你还是快点将我放回,如今还没有外人发现,尚有挽回的余地。”盛则宁用手撑着身子,想要挣扎起身,但是那迷药的效果还在,她的力气有限,很快就撑不住自己的身子,往前栽去。
谢朝宗及时伸手把她揽住,没有让她悲催地面朝下,摔到地上。
抱起她后,也不顾她气急败坏,谢朝宗温柔地摸了摸她的脑袋,又把她按到自己胸膛上,声音轻轻道:“怎会没人发现呢,说不定封砚已经知晓了。”
盛则宁愣了下。
谢朝宗仿佛是从这里寻到了什么乐子,不等盛则宁开口问,就兴高采烈地继续说道:“你想必还没发现吧,但凡你出门,身后总会跟着几条尾巴,也亏他们要藏匿身形,不想被你发现,所以总是不敢跟得太近,这才给了我机会,不过,他们许久等不到盛家马车动身,定然会有所怀疑,进林子去一探,然后——就发现,你不见了。”
虽然不能亲眼目睹,但是谢朝宗也能想象到封砚听到这个消息后那副惊愕的模样。
明明想要时时刻刻放在眼皮底下,却只能偷偷摸摸在暗处看着,就怕她哪一天会不告而别。
可他千防万防,也没有防住盛则宁真的会消失。
“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吧,你猜,封砚他会来找你吗?”
“无聊,我才不和你赌。”盛则宁用头顶住他的胸膛,恨恨道:“谢朝宗,我绝不会跟你走!”
谢朝宗自然而然地略过她后半句话,反而问她:“为何不赌,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盛则宁停下了无用的挣扎,不禁怀疑道:“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谢朝宗的声音里有太多自信,就好像注定会看见她的失败。
外头的马忽然长嘶一声,马车一个急停,险些把两人都摔了出去。
“啧。”谢朝宗稳住两人的身子,扯了扯嘴角,“倒霉,绕了那么多路,竟然还碰见这些人了。”
盛则宁听见了外面很多哭嚎的声音。
有妇人、有小孩,还有男人。
她扭过身体,撩起车帷,看向外面。
目光所到之处,都是一些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人,老少皆有。
他们互相搀扶、跌跌撞撞往前行,仿佛只是就要行将就木,毫无生机。
“救救我们!——”
“救救我的孩子……”
盛则宁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会如此凄惨!”
谢朝宗把她身上的兔毛袄子裹紧了一些,像是怕外面的秋风会冷着她一样,“我早些时日就听闻西涼王病重,算算日子,他也该死了,所以西涼必然大乱,这些兴许都是从鸿雁关逃过来的流民……”
*
“官家,您觉得这样如何?”
封砚闻言,慢慢抬起眼,书房里站着的都是举足轻重的重臣。
他们在为新政的细节吵闹不休。
世家唯恐变动,会瓜分掉他们原本的利益,而清流出身的就担心不能从世家门阀手里抢得一席之地。
两方的人各持己见,僵持不下。
他便在这个时候出了神。
今晨起他就一直心神不宁,也许是因为盛则宁今日出了城,要去盛家的别庄。
别庄虽然离上京城不远,仅半日的路程,可是他还是不免会担心中间出什么岔子。
手指轻轻敲了敲桌案,封砚让自己平复下那焦虑的心情。
“你们所言各有道理,只是这条新规不为世家也不为寒门,而是为百姓,众卿若都为了一己之欲,从中作梗,阻我新政……”说着,封砚撩起眼皮,不咸不淡地扫视众人。
就好像他总能游刃有余地把控住他们,而不会被影响分毫。
如此镇定自若的样子也显得他有些不近人情,就好像若是他们胆敢阻扰,必不会有好下场。
众人不由后背一寒,齐齐拱手告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