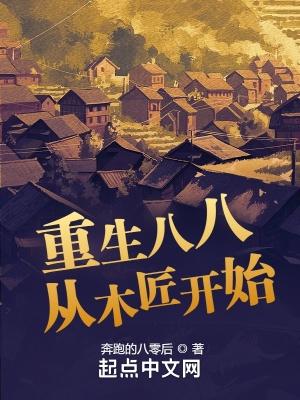鹅绒锁>我早就不喜欢你了,狗皇帝 > 5060(第11页)
5060(第11页)
瑭王一大早入宫,并不是来送什么佳礼进孝而是送来了一沓状纸。
「是你!」
魏皇后这才知道魏平会被南衙抓走,全是封砚所为。
她是一时气昏头。
想想也是,南衙府尹即便再怎么胆大包天,怎么敢动魏国公府的人。
哪怕盛则宁可以对付管修全、孙无赖之辈,也绝不可能凭她的身份告倒魏平。
「回母后,正是儿臣。」
「你抓的可是吾的亲弟弟,当朝小国舅,谁给你的胆子!」魏皇后一拍桌案,沉声巨响。
满殿的宫人叩首在地,口中惶恐道:「圣人息怒!」
哪怕不是她们的罪责,依然担心被迁怒在身。
「你们都退下。」
封砚让其余人退到殿外,只余留下皇后身边的内官和贴身宫女。
内殿沉闷寂静,就好像暴雨前潮热厚重的空气,让人呼吸都觉得困难。
封砚对着皇后跪下,身直如松,仪态从容,就似乎皇后的动怒都是他早有预料的事,他不慌不忙地开口,声音沉稳,如同那根最难以拨动的宫弦,音沉而质坚。
他缓缓道:「儿臣以下告上,且告之为亲长者,按律该以仗二十,孔内官,就由你来行刑。」
孔内官吓了一跳,下意识去看皇后的脸色。
魏皇后沉眸冷面,声音冰冷:「我儿如今大有本事,是觉得吾不敢罚你,所以也学会了先斩后奏?」
「儿臣并无此意。」封砚垂下眼睫,长睫遮去他墨眸,像是恭敬而卑微,又似坚决而不退让。
「你执意要如此?」魏皇后手握在扶臂上,指尖几乎要为此折断。
「请母后成全。」
封砚的坚持让魏皇后的气恼到了极限,她对身边的孔内官道:既然如此,那好!」
孔内官手颤了颤,下意识躬背附身想为瑭王说几句情。
魏皇后一挥手,打断他意图,厉声道:「去,如他所愿!」
宫中的廷杖律尺那都是用来处置犯事宫人,何曾用到过尊贵的主子身上。
孔内官捏着三指宽的律尺,冷汗簌簌往下落。
魏皇后盯了他一眼,孔内官不敢再迟疑,只能走上前。
封砚早已经脱去外衫,只着了中衣跪在正中,月绫里衫单薄,并不能阻挡什么,这一尺下去必然伤着皮肉,孔内官心里叫苦不迭。
这对母子斗法,偏偏让他做了大恶人,这叫什么事啊!
孔内官痛苦悔恨,自己为何要出现在这里,要是去送那盛三姑娘多好。
人越是想逃避某件事,那事必然迎头撞上来。
「还愣着做什么!」魏皇后正在气头上,一刻也不能等,见孔内官拖拉更是怒不可遏。
「圣人……」孔内官支支吾吾,「这二十尺下去必见血啊。」
魏皇后冷声:「胆敢状告亲长,必受切肤之痛。」
封砚如此忤逆她,让她感到了威胁,此时不出这口气,她的心就无法平静下来,更听不进任何话。
孔内官劝不动皇后,只能咬咬牙,对封砚躬身道:「殿下还请容忍一二。」
「多谢孔内官。」封砚垂下眼,并无任何要为自己求情的意思。
这是铁了心要受这二十律尺。
孔内官无法在这律尺上留情。
他为皇后掌管后宫刑责,动用刑罚少说也成千上百来次,这一尺下去是如何、二十尺下去又是如何,魏皇后一清二楚,他若是留了情,皇后定然要怀疑他不忠,是否已经偷偷偏向瑭王。
这是孔内官万万不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