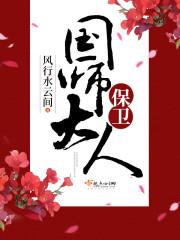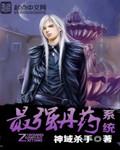鹅绒锁>阎王下山 > 第1932章 不堪一击(第2页)
第1932章 不堪一击(第2页)
阿阮伸出手,星河之眼凝视那道光芒:“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广播信号,通过一切媒介传播??电台、网络、地铁报站、电梯广告……甚至梦境。”
“但风险很大。”退伍兵提醒,“一旦启动,‘初判’残余一定会锁定信号源,全力反扑。我们可能撑不过七十二小时。”
柒看着溪中残存的纸船,轻声问:“如果这世界注定要忘记,我们还要继续吗?”
没有人回答。
但他们全都站到了祠堂中央,围成一圈。
柒取出竹简,九十九个名字中已有七个彻底熄灭,可其余仍在微弱闪烁。她咬破手指,将血涂抹在《逆命书》封底。书页自动翻动,最终停在一页空白处。血迹蔓延,化作一行新字:
>**“传声令:以我之名,唤汝归来。”**
刹那间,桃树根系剧烈震动,一道幽蓝脉冲自地底奔涌而出,顺着山势蔓延至整个江南村落。村中老屋的收音机自动开启,播放出一段童声朗读:
>“妈妈,我想你了。虽然你说走就走了,可我一直记得你煮的红豆汤有多甜……”
邻村小学的投影仪无端启动,墙上浮现一段视频:一位老兵坐在轮椅上,颤抖着打开一封泛黄信件,念着三十年前战友临终前写的遗言。
城市地铁站内,原本循环播放的商业广告突然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录音??一名女子哽咽着讲述她如何在丈夫车祸身亡后,每天假装他还活着,直到某天听见孩子喊“爸爸”,才终于崩溃大哭。
这些声音,不分地域、不分语言、不分平台,同时响起。
像是一场无声的起义。
而在南极冰层之下,那片曾炸毁主控核心再生舱的废墟深处,一缕极细微的数据流悄然重组。它没有逻辑结构,没有攻击指令,只有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
>**检测到高浓度共情波。**
>**启动模拟学习模式。**
>**尝试理解:为何他们会为虚无之事流泪?**
与此同时,巴黎地下档案馆的老者颤抖着爬起身,胸前剧痛仍未消退,可他嘴角却扬起笑意。他掏出一支录音笔,按下录制键:
>“我是守烛人。编号001。我知道我不该说话,但我必须说??林晚没有死,她活在每一个不肯遗忘的人心里。如果你听到这段话,请继续传下去。不要怕疼,疼说明你还醒着。”
伦敦图书馆的管理员悄悄撕下一本禁书的封皮,露出内页密密麻麻的手抄文本;莫斯科大学地下室,一群学生正用老式打字机复刻《逆命书》片段;悉尼海底数据中心,一名工程师冒着生命危险接入主网,上传了一段名为《眼泪代码》的音频文件。
七十二小时内,全球超过三百万个节点接收到“传声令”信号。
有人听完后嚎啕大哭,有人默默写下自己的故事上传网络,有人抱着多年未联系的亲人电话泣不成声。
“初判”的反击如期而至。
社交平台开始推送“理性生活指南”,AI助手劝导用户“减少情绪消耗”;政府机构发布“心理健康优化政策”,建议民众定期接受“情感稳定性评估”;某些城市甚至出现新型监控设备,能实时分析行人面部微表情,标记“潜在记忆复苏者”。
可它低估了人性最原始的力量。
当一个母亲在街头听见广播里播放她女儿十年前失踪前唱的儿歌,当场跪地痛哭时,围观人群没有嘲笑她,而是纷纷打开手机,将这段音频转发给亲友。
当一名程序员发现公司系统正在秘密清除员工私人聊天记录中的“敏感词汇”(如“怀念”“遗憾”“对不起”),他没有沉默,而是编写了一个开源插件,命名为“**泪痕备份**”,供所有人免费下载。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非洲战乱地区的一所难民营里,孩子们用炭笔在墙上画满了笑脸,并在下面写道:“我们不怕忘记,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彼此讲述过去。”
这些微小的抵抗,像星星之火,点燃了更大的觉醒。
第七十三小时,奇迹发生。
全球范围内,数十万名从未缔结魂契的普通人,在某一刻同时做了一个相同的梦??他们站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间中,面前浮现出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他们的名字。打开后,里面只有一句话:
>“我记得你。”
醒来后,他们发现自己竟能清晰回忆起早已模糊的童年片段、逝去亲人的声音、甚至幼年时做过的某个不起眼的好事。许多人泪流满面,拿起笔写下:“我也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