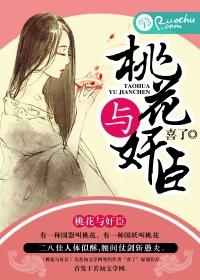鹅绒锁>师叔,你的法宝太不正经了 > 第977章 清算(第1页)
第977章 清算(第1页)
我,过去?
季鸿旭内心恐惧。
若是平时,老祖叫他,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笑脸相迎地快步赶过去。
但现在,抬头便是面对季延南那宛若阴鹫的眼神,他不知怎的,竟然双腿难以移动半分。
“老祖,我,我……”季鸿旭语无伦次。
“无妨,你过来便可。”季延南喘了口气,朝着他笑了笑,声音平缓,甚至还带上了一丝温和,仿佛只是在叫一个不懂事的晚辈。
季鸿旭一辈子都在揣摩人心,尤其是这位老祖的心意,这也是他能上位成代族长的主要缘。。。。。。
山雨初歇,晨雾如纱,缠绕在启言书院残垣断壁之间。那株老槐树的枝干上,还挂着昨夜“共名”潮退后留下的光尘,像是星屑凝成的露水,在微风中轻轻颤动,偶尔滴落一粒,便在泥土里绽出一朵小小的言铃花,旋即又悄然枯萎,化作一道淡痕,仿佛只是大地的一声叹息。
盲女仍坐在石台边,双手抱着膝盖,脸贴着冰冷的石面。老人??雪山??已经不在了。他的身体随着最后一道波纹消散于天地,连骨灰都未曾留下。只有胸前那枚铃铛徽章静静躺在石台上,铜绿褪尽,表面光滑如镜,映着初升的日光,竟隐隐有无数细小名字在其间流转,如同呼吸。
她听不见他的声音了。
可她知道,他还活着,在每一阵风里,在每一声呼唤中,在每一个敢于说出“我”的唇齿之间。
她缓缓伸手,指尖轻触铃铛。刹那间,一股暖流自指尖涌入心口,像是有人隔着岁月握住了她的手。她闭上眼,耳边忽然响起一个极轻的声音,不是从外而来,而是从她心底浮起:
“你听见了吗?”
是雪山的声音,温柔、疲惫,却带着笑意。
她点头,泪水无声滑落:“听见了……所有人都在说话。”
的确,整个神州都在“说话”。
不只是人声,还有物语。
一块被遗弃的碑石在荒野中低吟自己的铭文;
一只锈迹斑斑的铁剑在古墓深处震颤,诉说主人战死前未尽的遗愿;
就连那些曾被焚毁的典籍残页,也在灰烬中重新拼凑出字句,随风飘散,落入识字者梦中。
言语不再是权力的附庸,而成了存在的证明。
但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觉醒。
北方边境,一座废弃的正音司旧址上,黑烟袅袅升起。十余名身披黑袍的人围成一圈,中央燃着一簇幽蓝火焰,火中焚烧的并非柴草,而是一本本从民间搜刮来的《心录书》与私人日记。他们口中念诵着早已失传的禁咒,试图以“逆鸣诀”斩断“共名”与现世的联系。
“言生于心,灭于火。”为首者低吼,“烧尽私语,天下归静!”
火焰骤然暴涨,竟将半空飞过的几粒言铃花光尘吞噬。然而就在他们以为得逞之际,火堆中忽然传出婴儿啼哭般的声音??那是被烧毁的书中亡魂的哀鸣。紧接着,灰烬腾空而起,凝聚成一张张模糊的脸,齐声质问:
“你们凭什么替我们沉默?”
黑袍人惊骇后退,可那些灰烬之脸如影随形,最终扑入他们口中鼻中,令其七窍流血,倒地抽搐。临死前,他们嘴唇开合,竟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自己一生最不敢承认的秘密:
“我曾在肃言使面前告发亲弟……只为求一官半职。”
“我烧过三十七本《家史》,只因怕祖上罪名牵连子孙。”
“我不是忠臣……我是懦夫。”
他们的尸体化作焦炭,而灵魂却随着风,飘向西南,汇入泪碑的水滴之中。
与此同时,南方某座小镇的市集上,一名少年站在茶楼高台,面对众人朗声道:
“我叫林九,父亲是十年前‘削形诀’中被抹去名字的三百城民之一。他曾写信给朝廷,控诉赋税不公,结果全家被列入‘失序名录’。那天夜里,官兵破门而入,母亲抱着我藏在灶底,父亲被拖出去时还在喊:‘我说的是真话!我存在!’”
台下寂静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