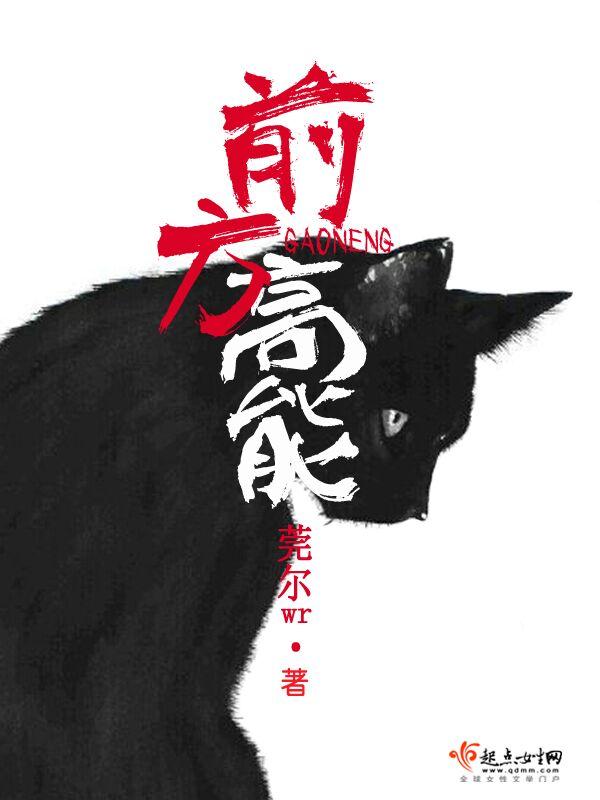鹅绒锁>野渡 > 8090(第19页)
8090(第19页)
nbsp;nbsp;nbsp;nbsp;他一连说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对不起。
nbsp;nbsp;nbsp;nbsp;姜宝梨都有点手足无措了,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说她没有不开心,没有不舒服,好像都没有办法安慰他失控的情绪。
nbsp;nbsp;nbsp;nbsp;最后,她也只能陪他一起哭。
nbsp;nbsp;nbsp;nbsp;“你到底干什么啊。”
nbsp;nbsp;nbsp;nbsp;“你这样,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
nbsp;nbsp;nbsp;nbsp;她一哭,司渡瞬间就控制住了自己。
nbsp;nbsp;nbsp;nbsp;他红着眼睛,一脸破碎的表情,找了纸巾给她擦眼泪:“是我的错。”
nbsp;nbsp;nbsp;nbsp;“我说了我不介意,不介意!”
nbsp;nbsp;nbsp;nbsp;姜宝梨攥住他结实的手臂,盯着他的眼睛,“刚刚的一切,我很享受,很舒服,你难道感觉不到吗?我很喜欢和你做…”
nbsp;nbsp;nbsp;nbsp;不,不只是肤浅表面的身体的欢愉。
nbsp;nbsp;nbsp;nbsp;司渡规划着更加阴暗的想法。
nbsp;nbsp;nbsp;nbsp;他不是泄欲,他是要占有、污染她,永永远远地…禁锢他。
nbsp;nbsp;nbsp;nbsp;是这种可怕的想法,让他的身体和灵魂在极致欢愉的时刻,伴生了巨大的痛苦。
nbsp;nbsp;nbsp;nbsp;司渡指腹抚摸着她漂亮的脸蛋,痴迷地看着她:“宝宝,不管是谁,都不能拆散我们,你要答应我这件事。”
nbsp;nbsp;nbsp;nbsp;“我答应你。”姜宝梨毫不犹豫地应下来,真心真意。
nbsp;nbsp;nbsp;nbsp;她知道司渡极其缺乏安全感,只能尽可能地给够他,他所需要的一切。
nbsp;nbsp;nbsp;nbsp;后半夜,司渡的服务意识爆表了。
nbsp;nbsp;nbsp;nbsp;或许是处于愧疚,自卑、自惭形秽,他给为姜宝梨清理身体,帮她放水泡澡,给她吹头发…
nbsp;nbsp;nbsp;nbsp;就像小狗一样从后面搂着她睡,迷迷糊糊中…还在吻她。
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缅东掸邦,沈毓楼刚下飞机,便感受到了一阵强烈的热带气流。
nbsp;nbsp;nbsp;nbsp;空气暖烘烘的,落机没多久,沈毓楼的白衬衫就汗湿贴在了后背上。
nbsp;nbsp;nbsp;nbsp;很热,也很闷。
nbsp;nbsp;nbsp;nbsp;街边,摩托车在狭窄的街道上穿梭,喇叭声此起彼伏。
nbsp;nbsp;nbsp;nbsp;手机软件显示,他要叫的车已经停在了附近。
nbsp;nbsp;nbsp;nbsp;沈毓楼环顾四周,在远处街角看到了对应车牌号的出租车。
nbsp;nbsp;nbsp;nbsp;一辆老旧的丰田卡罗拉,车漆已经有些斑驳。
nbsp;nbsp;nbsp;nbsp;然而,驾驶座上却空无一人。
nbsp;nbsp;nbsp;nbsp;沈毓楼拖着行李箱走过去,才看到一个穿工字T的瘦高男人,撒完尿从小巷里走出来,边走边提着松垮的短裤。
nbsp;nbsp;nbsp;nbsp;东亚人面孔,深眼窝,鼻梁挺直。
nbsp;nbsp;nbsp;nbsp;本来应该是一张英俊清秀的脸,却因为常年待在热带,皮肤被晒得黝黑,胡子拉碴。
nbsp;nbsp;nbsp;nbsp;“不好意思啊,人有三急。”男人用流利的掸邦话对他说,“久等了,请上车。”
nbsp;nbsp;nbsp;nbsp;沈毓楼笑了下,用中文说:“没关系。”
nbsp;nbsp;nbsp;nbsp;男人这才抬头,认真打量了沈毓楼一眼。
nbsp;nbsp;nbsp;nbsp;翩翩如玉的浊世佳公子,来掸邦这地方干嘛?
nbsp;nbsp;nbsp;nbsp;“中国人?”
nbsp;nbsp;nbsp;nbsp;“嗯。”沈毓楼点头。
nbsp;nbsp;nbsp;nbsp;“巧了,老乡啊。”司机难得看到老乡,笑容多了点真诚,“上车吧。”
nbsp;nbsp;nbsp;nbsp;沈毓楼将行李箱放入后备箱,上了车。
nbsp;nbsp;nbsp;nbsp;“是东帝大酒店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