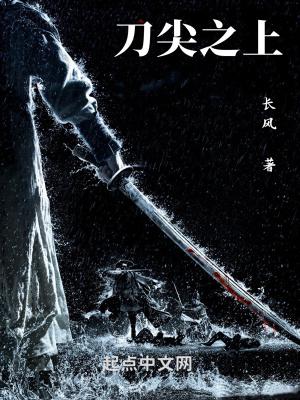鹅绒锁>【边州志】魏昭儿传 > 第3章 烙名(第10页)
第3章 烙名(第10页)
大胡子元帅一阵大笑,伸出两指遥指乙六,摇点着说道:“既如此,汝打算饶恕太守否?”
“不似!只是不能撒!”
“那汝想如何?”
一瞬,脸上颤着绷带的军士凶狠的盯着蹲在自己身边的太守夫人,看着她那白花花的身子,陈乐的心中猛地一紧,几乎立即就想到他要说什么。
“太守似七似男儿,则似死死,也不乎和老似则出。现在既然太守死人在此,似就想用似一用!”
不!!!——陈乐在心中猛地叫道,王老夫子他们则是继续死死按着他的身子。
“哦?乙六啊,汝可知吾之军规?”刘柱微微一皱眉头,捻着铁须,再次拉出一个长音,眯着眼睛,朝那名军士问道。
“似似道,但不早似母咔,似似似似似!望大似似似!”
那名军士立即一个抱拳,因为口齿漏风,都听不清在说什么——但即便听不清楚,只凭那腔调,语声,众人就能猜出他话里的意思:他是想要侮辱太守夫人——而就是在此时此刻,那些围在陈乐身旁的诸人中,居然还有人觉得庆幸,安庆自己无事,将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刘柱故作为难的说道:“吾早言,魏氏既为母吼,天道有伦,自有吼可交。”
“不过此吼尚未赐名,若说与人敦伦,却也可通。只是为母吼,为吾。为人,尚为太守之妇。汝要合之,需太守应允方可。”
他略作不快,似要拒绝,又话锋一转,转而朝陈乐问道:“子平啊?吾士与汝妇敦伦,汝意乎?”
他瞧着卫城太守,明知故问的问道。
陈子平被众人死死按住,捂着嘴巴,在心里大喊道:畜安敢辱我!畜安敢辱我!!!但是,但是……
“子平啊,吾知汝之愤,然,城中众老、幼,汝之满门,皆汝一念间乎。古,践者食粪,今,子平送妻,必皆千古之佳话矣。”
“子平,子平啊!!!”
王老夫子双手抓着陈乐几快气炸的双颊,使劲的揉着,搓着,颤声劝道:
“汝明乎,汝明乎???”
不,吾无法想明!吾无法想明!
陈乐在心中大喊,眼看着刘柱那依旧故作为难,眼中却充满戏谑,瞧着自己的眼神,还有昭儿,昭儿!!!
他看着魏氏,看着娘子惊恐,哀求的望着自己的目光,她那不知为何,是害羞——是的,一定是因为这赤裸见人的羞耻——而红红的双颊,蠕喏颤抖的红唇。
陈子平一下一下的喘息着,瘦瘦的喉颈在三捋长须下不断起伏着,明明,明明,娇妻就在自己身边,昭儿就在自己身边,任何男人,只要是个男人就不会答应!
但是,但是……
“子平!子平!!!”
夫君,夫君……魏氏望着自己的夫君,眼中含着泪滴,几近绝望的摇着螓首,不要……不要……
但是,但是……
吾除为人之夫,亦是一郡之守,一城之主,一族之肱骨,是人父,是吾孙儿之爷……
陈乐咬紧牙关,心中都如在滴血一般,在爱妻的注视下,在众人的劝说下,在刘柱,还有那个疤面副将,还有那个被自己割去口鼻的军士的嘲讽的注目中,缓缓的,阖上了双目,眼角处都被泪水浸湿,似乎流出什么东西般,轻轻的,点了点头。
“主愿予!”
立即,陈乐身旁的一人就赶紧高呼道。
“哦?然否?”而那刘柱却似还不满意,竟似要他亲口承认才可。
“子平,子平啊!”
夫君!夫君!
“咯咯……咯咯……”陈子平咬着口中的白牙,都将自己的嘴唇咬出血来,“愿予……”当他终于把那两个字痛苦的念出的之后——不,陈乐自己都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
不!
不!
魏氏在心中娇呼着,绝望的喊着,她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夫君要如此待己,如此待己!
自己可以为了夫君,为了杰儿,为了峰儿,为了玉儿,为他们牺牲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