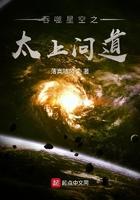鹅绒锁>风雨里的罂粟花 > 第5章 下(第6页)
第5章 下(第6页)
我看她这样,一开始也根本一点胃口都没有,于是也跟着基本上没吃东西没喝水。
可当到了这天的后半夜,我整个人起身去洗手间的时候,一起身突然双眼一黑,不仅有些体力不支的感觉,当我跑去厕所方便的时候,我尿出来的尿,竟然还有点黄中透着红,那味道更是骚臭难闻,尿液溶于便池里的水之后,一股镀在尿液上的红色物体,便朝着马桶最底下聚集到了一起,堆成了一摊殷红色的东西——这怕是连着没吃饭也没喝水,给自己弄得血红细胞过多,而且也把我自己虐待到了有点低血糖的状态。
于是,我赶忙回到我的屋里,从电脑桌抽屉中翻找出了一条士力架,才算把体力缓过来。
连着一天不吃饭不喝水,我这一个身高八尺有余、身体壮硕的男的都这样,赵嘉霖再怎么说,也是一介女流之辈,而且从小到大又是娇生惯养,她这么不吃东西怎么行?
而这会儿,她又一次沉沉睡去。看着有些许面呈菜色状态的赵嘉霖,我暗暗在心里做了个小决定:
等第二天清晨她睡醒的时候,我便下楼热了一杯牛奶麦片,看着她依旧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不说话的样子,我又急又火地对她问了一句:“你吃点东西吧,行不行?”
她依旧沉默。
“是我错了,嘉霖。我没保护好你……而且我承认,因为我对周荻的恨,我牵连到你了——在‘知鱼乐’你被……你被那什么的时候,我是有一点看热闹的心思。但是我现在知道我错了……你要怎么对我、怎么惩罚我都可以!你的手枪就在走廊对面我那屋,你要是觉得不解恨,你给我两枪!但你别折磨自己行吗?你得吃点东西啊!咱们俩能从‘知鱼乐’里活着走出来就不容易!你先吃点东西行吗?”
她终于低眉垂眼看了看我,又紧闭上双眼,然后再次抬起视线,继续望天。
于是,我倒吸一口气,端起杯子,含了一大口牛奶麦片粥,然后放下杯子,走上前去,捏着她的下巴,用拇指和食指捏开了她的樱口,接着我迅速地直接把我的嘴巴抵在了她的软唇上,用舌头撬开了她的牙关,嘴对嘴地把口中的牛奶燕麦送到了她的嘴里;
而就在我和她的嘴唇贴上的时候,原本已经成了行尸走肉一般的赵嘉霖,却仿佛突然有了生机,先是整个人身子往下一沉、一软,可紧接着,却皱起眉头攥紧拳头,用双拳在我的身上一通猛砸,见我还没从她的身体上起开,就改砸为掐,用着她纤细的指甲,在我的后背和脖子上一通抓一通挠之后,用她的指甲侧刃,拧螺丝一样揪其我的脖子上的两块肉,拧着在上面掐出来一个”米”字,这种钻心的疼,真不亚于被缝衣针连续猛扎;可在我把牛奶送入她的口中之后,她的身体却似乎也从我的身上接收到了体温、以及从我口鼻中呼出的热气,于是,她完全是出于本能地,把口中的东西咽进了肚子里,并且条件反射地吸吮了下我的舌头,可当她反应过来我的舌头已经入侵了她的口腔里之后,又恶狠狠地盯着我,一拳砸在了我的胸口。
我看她的状态,连忙收回来舌头,并且整个人都朝后面闪了个趔趄——多亏我反应快,要不然恐怕我半条舌头都得被她咬掉。
而她整个人也撑着胳膊,半坐了起来,继续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苦涩地长吁一气,站起身来,用手背蹭干了嘴角,看着她的凶恶目光,愧疚地说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想要……我不是想趁着你这样,故意想要占你便宜……但,我是看你一直不吃东西,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已经看着你被别人那样欺负过,我不能再看着你把你自己的身体给摧残坏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实在是有点不会安慰人,但我也只能说道:“你放心,昨天晚上在‘知鱼乐’里发生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跟人说出去!跟任何人都不会!我觉得……既然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也没办法……既然你我都活下来了,这很不容易……那么,咱们俩是不是就应该好好活着?”
赵嘉霖怨恨且痛苦地看着我,一股清泪从她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但她也没哭多久,毕竟她身体里的水分似乎没多少了。于是哭了会儿后,她整个人朝后一倒,又继续看着天花板不说话;
不过,当我再次端着盛满的勺子,放在她唇边的时候,她总算张嘴,等着让我喂她了;
而且,等我喂完了一杯牛奶麦片之后,她还总算下了床,自己去洗手间方便了一次,才回到床上,自己给自己盖上了毯子,继续双眼望天躺着。
——这下,我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但我这时候其实还不知道,我放心放得有点早。
中午的时候,我又给赵嘉霖热了一杯牛奶麦片,她也把那杯全都喝了,除此之外,又喝了一杯蜂蜜水。
看她两顿都能将流食打扫干净,我觉得她的精神状态应该大抵是开始缓过来了,但看着她仿佛一天之内就消瘦了一圈的模样,我心说,怎么也得给她弄点正经的碳水和蛋白质来源,因此,我便在晚饭时间之前的一小时,给家附近的一个小餐馆打电话,订了两份洋葱肥牛跟照烧鸡腿便当。
好死不死,今天在那家小餐馆值班的,是他们家的老板娘——以往他们家男老板在的时候,如果是住在周围的食客打电话订餐,那么那位憨厚的男老板就会自己开车,给周围的人亲自送餐,我先前上学的时候,一到假期,想起来了就会跟美茵一起订他家的炒菜或者便当吃,说起来,那位大叔也算是看着我俩长大的;后来那位大叔大概是四五年前,经人相亲介绍,娶了一位胖胖的妻子,成了他家餐馆的老板娘,那女人长得虽然胖了点,但是五官倒还算精致好看,然而,这女人实在是太过于能算计,为了节省店里的人工成本,从来不会答应订餐人免费送餐,哪怕就在他家餐馆对面也不行,想送餐就得找外卖平台APP,网上一派单,不一定是就近优先派单送餐不说,还得多花十块钱的送餐费——如果订的东西多的话,我也就忍了,两份便当加一起最多也就二十多块,再多花十块钱,怎能不让人多算计算计;除此之外,订餐的时候想要一次性餐具和餐巾纸也得多给三块钱的小费,订超过一份盒饭套餐却通常就给一份泡菜和一份例汤、如果再想多要也得多花三块钱。
所以,在我花了二十分钟跟那个胖女人苦口婆心地说,我们这边有病人、走不开,哪怕一次性餐具和随餐的泡菜、例汤都可以不要,只希望店家能帮忙送餐,但这女人还是油盐不进。
我一寻思那家店就算是从我家门口步行出发,最慢也就是十五分钟就到了,她不给送餐也就算了,于是快到了餐备齐的时间,我便穿了外套下了楼,还拿了车钥匙,自己开着车去到店里取得的餐。
——当然,也多亏了我是开着车去的。
我一脚油门,花了不到三分钟到了店里,连等餐加付账用了差不多五分钟,又一脚油门花了两分多钟回到了家里:而就在这将近十分钟时间里,家里发生的情况,差点让我控制不住:
等我回到家里,一开门,还没等我把鞋脱掉的时候,我就见着美茵的那间卧室的门开着,而洗手间的门也开着,刚开始我还以为赵嘉霖是因为着急去洗手间而忘了关门,所以我脱了鞋后,还很闲庭信步地去把外卖餐盒拿到了厨房的操作台上;可就等我准备从碗架上拿出两个小碗、一碗盛些饭菜、一碗舀些酸辣汤的时候,我却听见水流哗啦啦的声音持续不断——我一回头,意识到自己涮洗了一遍碗筷之后再关了水龙头,水流的声音却还在,我这下才反应过来,原来是楼上好像一直开着水龙头没关……
我登时放下手里的一切东西,快步跑上楼去,直接跑进了洗手间里——一进去,便看见自己把自己全身上下脱得只剩一件黑色文胸、一条黑色三角帆布内裤,整个人摊跪在我家的洗手池前,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并且,她的右手,正握着一支刮胡刀片——那是我的刮胡刀的备用刀片……我的神啊,我怎么就忘了把这东西收起——而她的左手的手腕,在她原先留过一条旧疤痕之上,已经被整整齐齐地割开了一条鲜红的血口;
她还将那只手,放进了封闭了通水阀的白瓷洗手盆里,龙头里温热和暖的水,源源不断地流出、然后把洁白的水盆逐渐灌满;温水冒着飘飘热气,浸在她的伤痕之上,让那些鲜红的血丝,好奇又自由地从她的体内窜出、蜿蜒、再逐渐扩散,仿佛刚刚破土而出的鲜红花朵,又似一束束绽开在白色天空中的绚丽烟花;那殷红的花雨,在一盆水的每一立方毫米之中占领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又手拉着手,将一盆透明的水彻底染成一眼朱砂温泉,然后,顺着洁白的陶瓷盆沿、纯白的大理石桌台,沿着她那嫩白的胳膊和腋窝,流淌到似玉似酥一样的全身,并继续汇集在地上,最终淌入肮脏的地漏管道里,最终发烂、发臭;甚至,迸溅到了她惨白的脸颊、下巴和嘴唇上,恰似漫天白雪之中点缀了几朵樱花,随后那些混杂着她的鲜血的狡诈的水珠,又一股脑化成白汽,笼罩在镜子上、最后又会凝结,并再次变成纯净澄澈的水珠。
——而这一幕被蒙上凄惨与唯美的愚蠢幻象,最终需要被我打破:“你干什么!你疯啦?”
我大叫了一声,立刻从毛巾架上抄起了一条浴巾,并立刻抱起把手腕泡在水里的赵嘉霖;
在我将她抱起的那一刹那,她总算再一次哽咽出了一声,“哼——啊”,随后,她眼睛里浑浊的泪水,跟着她右手上的剃须刀片一起掉落在地上;
而我已经没心思想明白,她这一声哽咽,究竟是因为我打断了她生命的流逝而心有不甘,还是因为我的出现和及时把她从正在踏入死亡的深渊里而发出的得救后的哀叹,我只是知道,我需要立刻把她的手臂用拧成一条粗绳的浴巾、贴着被她割开的动脉牢牢系紧;
紧接着,我也顾不上自己双脚踩湿,直接将她整个人抱着下了楼、并且重新踩上了我的那双棉鞋,回手把门先一反锁再一带,又抱着她,冲到我的车子旁边,勾着手拉开了车门;但等把她放在了后排座上,我才意识到她的身子近乎全裸,我也来不及多想,便只好把自己的羽绒大衣外套脱下,盖在她的身上,然后一脚油门,直奔民总医院——民总医院算是距离我家最近的大医院了,急诊系统也算得上整个F市最有效率的,并且大医院人多眼杂,每天生离死别的事情、因为各种事故而被送来的事情、以及各种医患纠纷在那里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所以赵嘉霖身上几乎一丝不挂地割腕、又被何秋岩送到医院的事情,在正经受着苦难的芸芸众生之间,应该不会被人注意;即便我记得,夏雪平那次被段亦澄打伤之后的血样是在民总医院被偷的,医院里可能会有‘天网’的人出入,此刻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一路开到100迈超速、连着闯了一路的红灯,直到抱着眼神有些迷离、眼球有些翻白的赵嘉霖冲进了医院大厅,也差不多花了十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