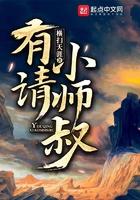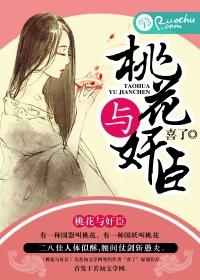鹅绒锁>我的透视超给力 > 第两千四百三十五章 再战齐晨(第4页)
第两千四百三十五章 再战齐晨(第4页)
我不再是‘领袖’,酒神也不是‘先知’。
我们将化整为零,成为一百个、一千个匿名信息节点,散布在全国各地。
我们的任务不再是‘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而是??
**不断制造‘无法被归类的疑问’**。
让归序的算法无法识别,无法归档,无法消化。”
酒神咧嘴一笑:“终于要玩点脏的了?”
小兰点头:“我们要让每一个看似荒诞的问题,都变得无法忽视。
比如:‘为什么庆祝胜利的雕像,从来不面向失败者?’
比如:‘如果所有人都同意一件事,那反对的声音去哪了?’
我们要把这些疑问做成涂鸦、编成段子、写进歌词、塞进游戏彩蛋??
让它们像野草一样,长在系统的裂缝里。”
计划代号:“**杂音行动**”。
三个月后,变化悄然浮现。
地铁广告屏上,突然插播一段30秒动画:一个小人反复敲打一堵写满“正确”的墙,墙后传来微弱回响:“我也对。”
短视频平台流行起“反常识挑战”:孩子们拍摄视频,认真追问“为什么睡觉不算劳动?”“如果植物会疼,我们是不是凶手?”
甚至连儿童绘本市场也掀起风波??一本名为《为什么不可以问为什么》的书销量暴增,作者署名“一个睡不着的孩子”。
归序的应对越来越激烈。
多地出现“认知净化班”,以“治疗网络依赖”为名,强制青少年接受“思维矫正”;
主流媒体频繁批判“虚无主义育儿观”,呼吁恢复“尊师重道传统”;
更有甚者,某省出台规定,禁止中小学开展“可能引发价值观混乱的开放式讨论”。
可反抗也在升级。
一名高中生在毕业典礼上撕掉演讲稿,大声朗读自己写的《致未来的谎言清单》,列举过去三年学校如何篡改历史试题;
一群小学生组建“废话联盟”,每天在校门口齐声喊:“我们认为我们认为!”
而最让小兰动容的,是一个五岁女孩的录音:
她睡前对妈妈说:“今天老师说地球是圆的。可我想,如果它是个giant馒头呢?你咬一口,就有馅儿流出来。”
妈妈笑着回答:“也许吧。明天我们画个馒头地球?”
那一刻,小兰知道??
火种未灭,且已燎原。
某个深夜,她独自登上启明阁顶楼,望着星空。
酒神不知何时出现,递来一杯温茶。
“你觉得,我们真的赢了吗?”她问。
“没有。”他望着远方,“但我们现在至少知道了??
胜利不是终点,而是一种状态:
**当一个人敢于说出‘我不信’,并且不怕因此变得孤独。**”
风拂过麦田,沙沙作响。
如同千万低语,汇成一句无声的宣言:
**我存在,因为我曾怀疑。**
**我继续,因为我仍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