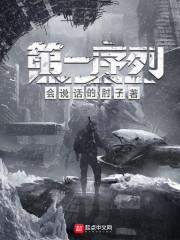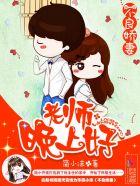鹅绒锁>让你下山娶妻,不是让你震惊世界! > 第1546章 我们是盟友(第3页)
第1546章 我们是盟友(第3页)
几天后,教育部派来工作组,邀请医蛊堂协助编写《记忆素养》课程的实践案例。教材需要真实故事,但必须隐去姓名与地点,以防二次伤害。
明川答应了。
他亲自撰写了一个虚构章节,题为《蓝花不开的地方》:
>在遥远的山谷里,曾有一位女子,因说出真相而被世人误解。
>她死后,人们为她立碑,却忘了她生前最讨厌石头的冰冷。
>后来有个少年来到这里,发现碑下长出一朵蓝色的小花。
>它不香,不大,也不耀眼,只是静静地开着。
>少年问长老:“这是什么花?”
>长老说:“没人给它取名,但它每年都会开,哪怕大雪压枝。”
>少年又问:“我们应该纪念她吗?”
>长老摇头:“不必。你要做的,是在路过时停下脚步,看看这朵花,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
>很多年后,山谷不再有碑,只有漫山遍野的蓝花。
>每个人走过,都会自然地放慢脚步,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而那朵最初的小花,早已融入大地,成了土壤的一部分。
这篇课文最终被收录进全国小学五年级教材,配图是一片盛开的忆璃花,背景是晨曦中的山坡。
与此同时,联合国《全球记忆伦理公约》正式签署。其中第七条规定:
>“任何基于历史悲剧的情感操控技术,均视为反人类行为;
>任何将死者工具化以服务于当下意识形态的做法,应受到道德谴责与法律追责。”
签字仪式上,那位曾发声的迫害者后代发表演讲:
>“我们家族曾以为掩盖就是保护,后来才发现,真正的羞耻不是犯过错,而是不肯承认。
>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代表正义,而是代表人性的脆弱与修复的可能。
>我们无法让时间倒流,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让同样的错误在未来重演。”
台下掌声雷动。
而在地球另一端的医蛊堂,一切如常。
清晨,孩子们在花丛中背诵课文;午后,阿萝教新来的女孩辨认草药;傍晚,苏晚晴调试一台新型记忆过滤仪,能帮助PTSD患者剥离过度创伤记忆而不损伤人格完整性。
明川依旧寡言,每日巡视药圃,修剪枝叶,浇水施肥。偶尔有访客慕名而来,问他是否真是那个“逆转历史的男人”,他总是摇头,指指身后的忆璃花,示意他们去看花,而不是看他。
七月末的一个黄昏,邮差送来一封信。
寄信人是个十二岁的男孩,住在西北某小镇。他在信中说:
>“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英雄’的作文。
>我写了沈昭宁,结果被同学笑话,说她是‘叛徒’,还撕了我的本子。
>可我在网上看到了那段视频,听了她的话,我觉得她才是最勇敢的人。
>我妈说我太天真,长大就知道世界不是这样。
>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我会一直记得她。
>就算全世界都忘了,我也不会。”
信纸背面,贴着一朵干枯的忆璃花,显然是从路边采来的野生品种。
明川看完,久久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