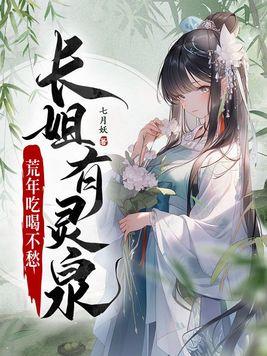鹅绒锁>大明:哥,和尚没前途,咱造反吧 > 第一千二百四十一章 数多了脚会麻(第4页)
第一千二百四十一章 数多了脚会麻(第4页)
他没有穿朝服,袖口挽了一寸,像是随意一走。
他在院门口停了一停,先看两块石,后看人群,最后看他儿子。
朱标迎上去,拱手:“父皇。”
“站得还稳?”朱元璋笑问。
“稳。”朱标正色,“今日学“收”,我收得最好的一次就在闭眼那一回。”
“闭眼也得稳。”朱元璋了一句,目光转向朱瀚,
“你这步盘术,朕看着像支小鼓。鼓点慢,人心慢;鼓点齐,人心齐。”
“皇兄说得好。”朱瀚笑,“不过鼓不在外头,在脚底。”
“脚底的鼓。”朱元璋咂了咂嘴,忽道,“你把第三块石也刻了罢。”
“等他们刻。”朱瀚摇头,“收得回‘这一句,由他们自己刻,才算数。”
“那好。”朱元璋不再多言,站到石旁,忽然对众人道:“谁今日收得最好,谁刻。
院里一阵静。
好一会儿,老人迈出一步,笑着摇头:“不是我。”
他把竹尺递给白榆,“小子,你刻。你今日那一句‘我到了’,我听见了。”
白榆吓了一跳,手心立刻出汗。
他看了看朱瀚,朱瀚点了点头。
白榆把竹尺握住,手指在尺背上一寸一寸摩挲了三遍,像是在确认某个重量。
然后他把尺当錾,手腕一沉,刻下第一个“收”字的点。
那点极小,却稳。第二笔一落,压住了石心里的一缕微响。
第三笔勾,他的呼吸悄悄吐出,线也随之收回在字里。
“好。”朱瀚低声。
“再写两个字。”老人道。
白榆咬了咬牙,“得回”两个字也落成。
他收手的时候,尺背轻轻一响,像石在答他。
他不自觉地笑了,一直抿得很紧的眉角在这一刻完全松开。
人群里爆出一阵压着声音的喝彩。
朱元璋看着这三个字,忽然转身,对朱标道:“你明日把这块石移去太学的石阶上,立三日。再把第一块、第二块也立回去。三日之后,收。”
“是。”朱标应。
夜色一寸一寸落下,院里点了两盏牛角灯。
灯光不强,照得石面上的刻痕像温着的水。
人群散去得很慢,像不舍得把这股子热从脚底收干净。
缪行把酸枣糖剩下的几颗分给了最后几个孩子,孩子们“谢谢”一声,跑着出了门。
“王爷。”阿槐从暗处闪到朱瀚身侧,低声,“那两拨看的人里,一拨走了,脚步散得快。另一拨走得齐,像在数。
“像在数,就让他们数。”
朱瀚的眼神比夜更静,“数多了,脚会麻。”
“要不要跟?”阿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