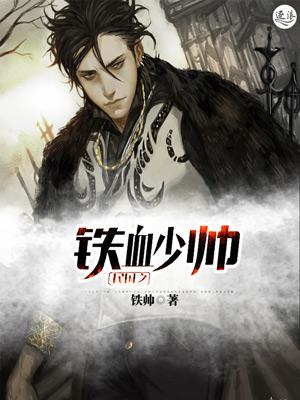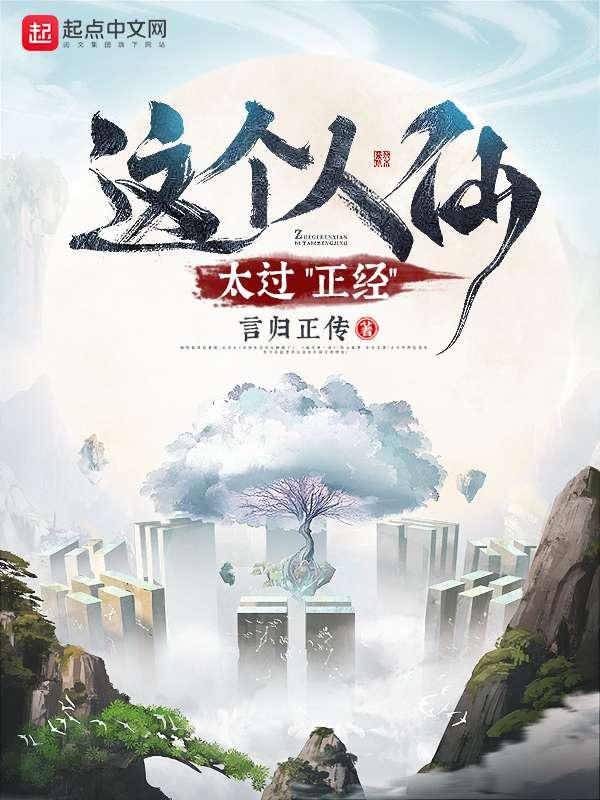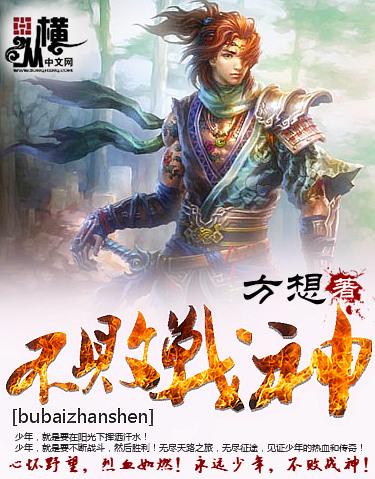鹅绒锁>都重生了谁考公务员啊 > 第656章孤独的融入天家(第2页)
第656章孤独的融入天家(第2页)
这条回复被系统标记为“高共鸣信息”,自动纳入教师培训案例库。
一个月过去,试点数据逐渐浮现。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所有提交的三百七十六个问题中,超过六成涉及家庭暴力、性别歧视、教育资源不公等现实困境。其中一个四川男孩写道:“我爸说我是累赘,因为我考不上重点高中。可我只是想当厨师,我不想死。”
这句话让整个团队彻夜未眠。
他们连夜升级预警模型,将“自我否定强度”列为一级风险指标,并与妇联、心理援助机构建立直连通道。同时,推出“匿名树洞”功能,允许学生用变声器提交问题,保护隐私。
与此同时,舆论风向再次微妙变化。
一篇题为《我们的孩子,正在学会沉默》的深度报道悄然走红。作者是一名退休中学教师,她在文中讲述了自己三十年教学生涯中目睹的种种“消失的问题”??女生不敢问月经相关知识,贫困生羞于申请助学金,留守儿童写信给父母却被老师当作“扰乱课堂秩序”。
>“当我们只教孩子标准答案,却不允许他们质疑生活本身,我们就是在制造顺从的机器,而非独立的人。”
文章末尾附上了“提问者计划”的链接。一夜之间,报名参与试点的学校增至二十三所,覆盖八省。
然而,暗流从未真正平息。
四月初,某省级教育督导组突然进驻甘肃临夏,宣布对“提问者计划”开展专项调研。名义上是“了解创新实践”,实则约谈多名授课教师,要求提供全部学生提问记录,并质疑“是否诱导未成年人挑战家长权威”。
消息传来时,江辰正在贵州山区回访一名曾因抑郁休学的女孩。她如今已是班里的“提问委员”,负责收集同学们不敢说出口的疑惑。见到江辰,她怯生生递上一张纸条:“我今天问了班主任一个问题??‘为什么女同学请假从来不告诉我们原因?’老师没生气,反而开了班会讲生理健康。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说话是有用的。”
江辰看着她微微发红的眼眶,握紧了那张纸条。
当晚,他拨通陈司长电话。老人沉默良久,才说:“上面有人担心,你们在培养‘不安分’的孩子。”
“可如果连不安分都不敢,那社会怎么进步?”江辰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
“我知道。”陈司长叹了口气,“但你要给他们台阶下。不如主动邀请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派专家参与课程评审,把过程做成公开直播。既展示诚意,也争取话语权。”
第二天,“破壁计划”官网发布声明:**欢迎任何机构和个人监督“提问者计划”,我们将全程开放教学实录、学生反馈与干预记录。**
此举引发巨大反响。数十位知名教育学者、心理学家联名支持,称其为“中国基础教育的一次勇敢试水”。更有家长自发组织“陪审团”,在线观看课程回放并打分评价。
五月,调研结果公布:无违规行为,无不当引导,部分课程设计获专家组“极具前瞻性”评价。官方通报中罕见提及一句话:“青少年的困惑不应被掩盖,而应被倾听。”
禁令解除那天,江辰带着一台移动设备走进临夏一所乡村小学。教室里坐满了孩子,还有十几位曾反对该项目的家长。
他没有讲课,只是播放了一段视频??十五分钟的剪辑,全是孩子们的真实提问与后续改变:
>青海女孩问:“为什么我要嫁人换彩礼?”三个月后,她父亲在村委会撤销了订婚协议。
>河南男孩问:“为什么我爸喝酒就能打人?”警方介入后,家庭暴力告诫书送达家中。
>广西双胞胎姐妹写下:“我们长得一样,可我喜欢画画,姐姐喜欢跳舞,为什么老师总把我们当成一个人?”班主任从此不再用“你们”称呼她们。
画面结束,教室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农站起来,声音沙哑:“我孙子上周问我,‘爷爷,你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课本里花木兰为啥能打仗?’我说……我答不上来。”他顿了顿,“但我现在明白了,他不是顶嘴,是在长大。”
掌声响起,夹杂着抽泣。
江辰走上讲台,只说了一句:“我们不怕问题,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问题背后,都藏着一颗不肯屈服的心。”
夏天来临之际,“提问者计划”正式纳入“萤火-极光”核心模块,成为所有新接入学校的必修启蒙课。与此同时,一项名为“反向课堂”的实验悄然启动??邀请农民工父母、留守老人、退役教师等群体,通过简易终端学习如何倾听孩子的提问,并给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