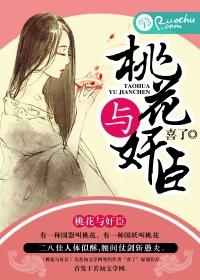鹅绒锁>阿兹特克的永生者 > 一千六百七十八章 朝贡之路银色的蜂鸟闪耀最遥远的胶人同族(第2页)
一千六百七十八章 朝贡之路银色的蜂鸟闪耀最遥远的胶人同族(第2页)
众人皆惊。阿力瞪大眼:“你……你竟亲手杀人?”
岳托擦刀入鞘,淡淡道:“他是叛徒。该杀。”
祖瓦罗缓缓收功,恢复正常神色,深深看了岳托一眼:“好孩子,你心里清楚得很。”
那一夜,无人再睡。尸体被沉入沼泽,马队连夜改道,绕行七十里,避开原定路线。祖瓦罗在火堆前画了一幅地图,用木炭标出几处险地。
“尚秃阿不会善罢甘休。”他低声道,“他不仅要杀岳托,更要毁掉这块铜印。只要铜印不现于朝堂,朝廷就不会承认亦儿古里卫有‘袭职’之请,岳托也就永远只是个流亡的野种。”
“那我们就让他亲眼看着铜印呈上御前!”阿骨打咬牙道。
“可开原卫守备极严,外族不得擅入官厅。”阿力皱眉,“除非有引荐之人。”
“有。”祖瓦罗忽然道,“我在开原有故人??一个汉人通事,姓陈,名文远。他曾受我救命之恩,答应过我三个请求。这是第二个。”
“你能信他?”
“不信也得信。”祖瓦罗冷笑,“我们已无退路。”
又行五日,终于望见开原城垣。城墙高耸,箭楼林立,城门处旌旗招展,明军巡逻不绝。马队停在十里外的驿站,众人换上粗布衣裳,扮作朝贡商旅。岳托依旧装傻,由萨哈连牵着马,口中喃喃自语,眼神涣散。
进城那日,天降细雨。祖瓦罗带着岳托与阿力,由陈通事引荐,进入贡院。贡院内人声鼎沸,各部女真、蒙古、朝鲜使者齐聚,递交表文,呈验贡品。轮到他们时,祖瓦罗取出铜印,双手奉上。
主考官是一名文官,姓李,瞥了一眼铜印,眉头微皱:“亦儿古里卫?此卫多年未朝,铜印也非现任都指挥使之物……你们是何身份?”
“小人祖瓦罗,林中萨满,奉亦儿古里卫先酋长沙古答遗命,携其子岳托前来袭职。”祖瓦罗沉声道,“沙古答已于去岁冬月遭逆臣尚秃阿谋害,铜印被夺。此印乃沙古答先祖之物,为证血脉正统,特呈御前。”
“沙古答死了?”李官惊讶,“可去年尚有一人持印朝贡,自称‘尚秀哈’,说是沙古答族侄,因沙古答病亡,代为摄政……你们可知此事?”
“那是篡位逆贼!”阿力怒道,“尚秃阿弑主夺权,伪造文书,欺瞒朝廷!此子岳托,乃沙古答唯一亲子,年十四,体格雄健,堪承父业!”
李官目光转向岳托。岳托依旧低头,嘴里嘟囔着听不清的话。
“他……真是沙古答之子?可瞧着不太聪明。”
“山神庇佑,智慧晚成。”祖瓦罗平静道,“但他血脉纯正,铜印为证。若朝廷不信,可令医官验血,或召旧日熟识之部民辨认。”
李官沉吟片刻,终道:“铜印需送京师礼部核验,表文亦需转奏。尔等暂留贡院,听候消息。若属实,明年春可得册封。”
众人松了口气。
当夜,贡院偏房。岳托终于卸下伪装,坐在灯下,手指摩挲着铜印。祖瓦罗走进来,递给他一碗热汤。
“你在想什么?”萨满问。
“我在想阿玛。”岳托低声道,“他临死前,是不是也很恨?恨自己没能护住部落,恨没能护住我?”
“他更恨的是人心。”祖瓦罗坐下,“尚秃阿曾是他最信任的兄弟,同饮一锅血酒,共猎一头猛虎。可权力面前,情义如纸。”
“所以……我也不能信任何人?”
“不。”祖瓦罗摇头,“你可以信,但必须先让自己强大。让所有人都不得不信你,不得不服你。”
岳托抬头:“怎么强大?”
“第一步,拿到官身。”祖瓦罗凝视他,“第二步,带回赏赐。第三步,杀尚秃阿,夺回卫所。第四步,让所有背叛者跪在你面前,亲口承认你是唯一的酋长。”
岳托默然许久,忽然笑了:“我以前以为,当酋长就是打猎、喝酒、分肉。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要一步一步,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
“聪明。”祖瓦罗轻拍他肩,“你比你以为的聪明得多。”
七日后,朝廷回音抵达:铜印经核验,确为永乐年间旧物;沙古答之子岳托,准予袭职,待来年春正式册封,赐七品武职,授“亦儿古里卫指挥佥事”衔,并允其率部朝贡,岁纳貂皮百张,马五十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