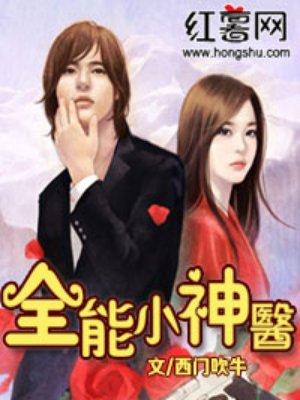鹅绒锁>女尊之渣女难为[快穿] > 80100(第23页)
80100(第23页)
“花朝节?二月十?五?那不是?过过了?今儿?是?二月十?九了呀。”
掌柜摊开?手来,苦笑着应道:“谁说不是?呢!可这新总统的一号手令,您猜怎么着?不说国家大事,单单一纸公文?,就规定把花朝节挪到二月二十?五了,以后节庆,就按这个日子过。”
“啊?”阿光的脸上,说不出是?笑还?是?为难,“可是?,节庆是?按着物候来的。十?五日欣欣向荣,百花绽开?,才叫花朝;到了二十?五日,百花都?开?过一轮了,风一吹,地上都?是?残瓣,看着不颓丧吗?”
“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掌柜咋舌。
阿光想起自?己看过的一篇志怪笔记。话说大唐时,武氏皇后以男子之身登基为帝。因其?牡马解祠(见作话),颠倒女子为尊的礼法,被人议论和轻视。于是?武后向百花耍威风,要百花在冬天开?放,为他庆寿。
如?今,李大总统强改节令,庆祝自?己的成功,真?像这个故事所讲的一般。
阿光皱着眉,又问掌柜:“这新的花朝节,要怎么个过法?”
“别的不太清楚,但?是?吩咐咱们梨园伶人和各家曲艺人都?备上拿手好戏,肯定是?要唱个大堂会的意思。”
“那是?得多大的堂会?平州有名的梨园子女,从早唱到晚,也未必能完事。又叫了那些小艺,吹拉弹唱的,排得开?吗?”
“哎,说不好。就是?这么吩咐的。”
阿光心领神会:“看样子,她们用?不用?是?一回事,我?们去不去是?另一回事。当真?不去,只怕是?不行。”
“正是?这个理。”掌柜又叹了口气,“您还?不知道。今早上,谕令传到三义社?的时候,李奶奶和闻小姐,都?已经上了火车了。本来约好去姑苏演出,早就定下的事,就该今早上走。可李大帅——唉,现在得叫大总统了。总之,派了顾副官,截停了火车,硬说她两个抗命反动,把人直接押了回来!”
“顾?”阿光愣了一愣。
“可不就是?……您那位……”掌柜欲言又止,但?意思总是?到了。
阿光冷笑一声,不阴不晴地道:“顾大人当真?好威风。想必若是?我?也不愿接这堂会的差事,她都?不会手软。带人一堵,锁链一套,配着我?今儿?穿的铁锈红衫子,可不就是?一出现成的《起解》?接下来,再给我?来个《三堂会审》,好给新总统邀一功。”
“杜老板,慎言哪。”
“哼,要杀要剐,叫她冲着我?。皱一下眉头,我?跟她姓。”
阿光眉毛倒竖,发火的样子倒比平时娇俏几分。
掌柜的听了这话,看这神情,明白了他的意思。
“杜老板,即便不愿……也还?是?继续忍着吧。开?罪不起。”
阿光不愿旁人跟着担惊受怕,便泄了一口气,貌似无奈:“唉,我?一介伶人,和她天差地别的,纵然心里怨恨,又能怎么样?”
掌柜点点头,应和一声。
来都?来了,阿光便跟掌柜的一起,整了戏码,誊写到戏单上。
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看不清戏神仙安排李大帅篡江山的戏码,究竟用?意如?何。
从这天起,平州城各家戏楼,都?挂出了停戏待定的招牌。各家伶人、艺人,都?在筹备这场铁蹄下的堂会,各自?忙碌。
阿光所在的饭店,真?是?神了。他在房间里吊嗓子、练武戏,动静虽大,却不会影响到旁人。
或许是?戏神仙有意为之,何妨物尽其?用??
只是?那以后,顾影再没有来找过他了。
有时候,当他练起《醉酒》、《断桥》、《汉宫秋》这些饱含幽怨之情的戏来,心里也会有些牵挂她。可转念想想戏中人的下场,这点绮丽心思,就成了警醒。
花朝堂会前夕,一切都?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二十?四日早,总统才通过教育部下了一道指令:从二十?五到二十?七日,连做三天堂会,每天分作上下午两场;期间开?国宴,招待新国民议会成员和社?会各界骄子;还?专门请来了友邦人士,将堂会的盛况通过最时髦的无线电波,传到华夏各地去。
于是?二十?四日下午,平州艺人齐聚在教育部里,商议堂会的戏码、艺人次序等事。
教育部是?主理文?化宣教等事的衙门。这次李大总统改换江山,这一衙门的人却没换,仍是?熟人熟脸,倒让梨园各家松了口气。一切商议定了,各家各自?做最后筹备,心里也终于踏实?了一点。
阿光她们的戏,定在第二天下午,招待商业人士的场合。
中午,戏班到场,简单吃了些饭,就开?始梳妆。阿光始终有种心神不定的感觉,似乎危险将近。
无意中,听到跟包的小丫头在悄悄议论。
“幸好咱们赶上这场,戏台下面都?是?旧世家。”
“要说最懂得戏的,还?得是?世家子女。而且,咱们三小姐也在台下坐着,想必咱家的角儿?看见了,就安心多了。”
阿光听了,心里更是?别扭,却不知由来。
待登了台,专心致志演完了戏,他才悄悄松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