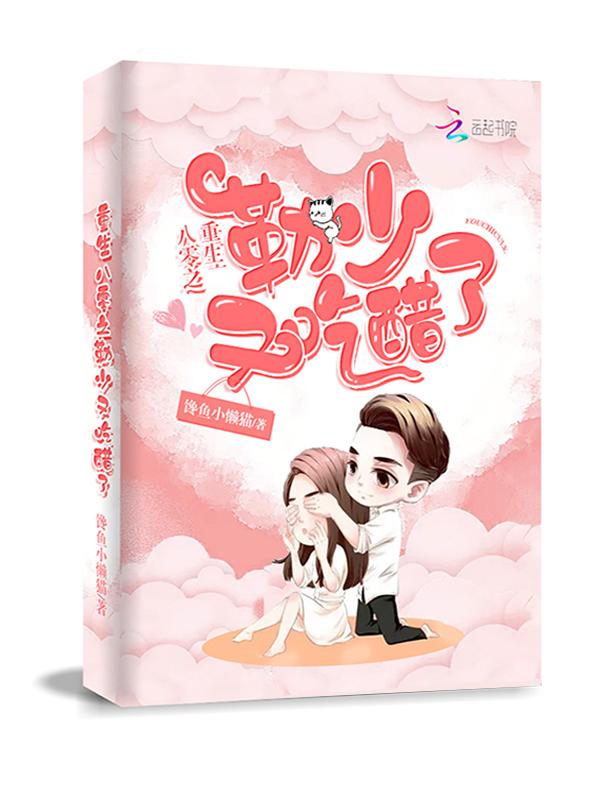鹅绒锁>【西方罗曼】高H合集(强制,乙女,美人受) > 纽约客4可名非名whatsinaname(第9页)
纽约客4可名非名whatsinaname(第9页)
少女盯着画的表情先是错愕,继而恍然,最后透出复杂,男人语气带上了几分漫不经心的炫耀,“Acquired
through
a
rather
delicate
negotiation
with
a…certain
family
of
aristocrats…in
Europe。
The
Old
World
bowing
to
the
New。”(从某个……欧洲贵族家族手里用了些……技巧……购得的。算是……旧大陆向新大陆俯首称臣。)随即落嗓沉了几分:“A
reminder
that
if
you
don’t
slay
the
dragon,
the
dragon
slays
you。”(用以提醒我自己,如果我不杀龙,就会被龙所杀。)
柰不禁抬头望向Fairchild。男人没看她,因白衬衫外仅着一件浅灰色的高定西装马甲,更显得身材挺阔。他一手微扶鼻梁上的金框眼镜,下巴微扬,目光犀锐地定在画上,像在审视一张死亡率表,而非欣赏一幅巴洛克名作。
客观来讲——再不情愿,柰也不得不承认——纯就相貌而言,Fairchild是个很英俊的人,甚至英俊得危险。大学时代大概是lacrosse或冰球或网球场上那种,带着几分贵族气质的疏朗风流,经过十余年商场的磨砺沉淀,如今收敛成一种冷静而算计的优雅。乍一看,他无懈可击,风度翩然,甚至能让人轻易生出几分信赖——但若是细看,就会发现他身上的每一处都太过精准,精准得不像是习惯,而更像是计算过的手段,就连偶尔有一两缕铂金色的发垂落在颊侧,也像是刻意为之,恰到好处地削弱了冷硬明锐,添上一丝不经意的松弛感,以令人放松警惕,可若你凝神观察就会发现,这松弛感中仍旧透着铂金冷淡的金属光泽,如同磨光的银器——精致、昂贵——却不带丝毫人该有的温度。
那双浅灰色的眼睛,乍看清透平和,色泽内敛低调,可若是盯得久了,便会意识到:那种清透的本质,并非柔和,而是彻底的冷漠——无机质,像是精钢与玻璃交错出的色调——光洁、明净、精密,却无法映照出任何温度。任何映入其中的色彩、情绪、微妙的情感流露,都会被悄无声息地吸收、分解,最终归于一种近乎虚无的透明,让人看不穿,摸不透,因而不知所措。
你甚至很难相信,这样的男人,竟然也会有情欲。
柰挪开目光,不动声色的拉开些距离,“You’d
think
that…after
all
th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