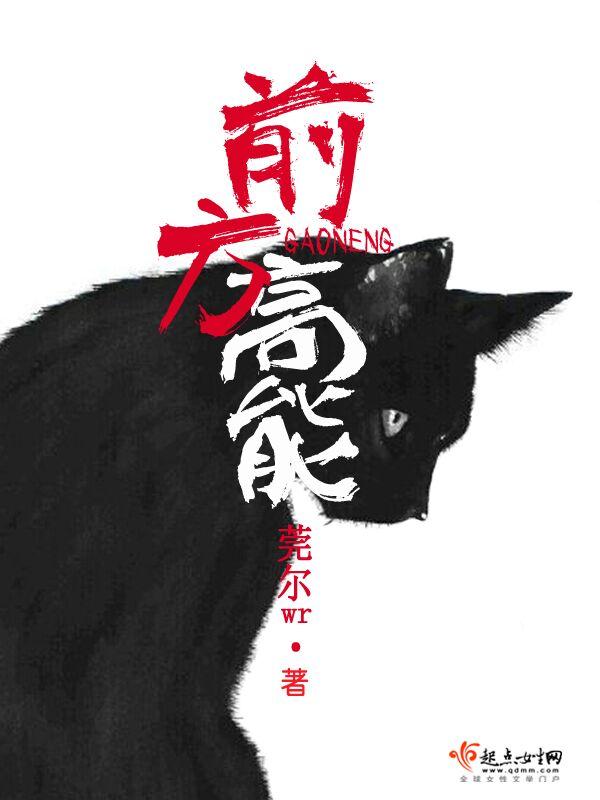鹅绒锁>萧玥谢靖 > 第4章(第1页)
第4章(第1页)
弘德帝面色骤变,手中茶盏重重搁在案上,茶水溅出,在紫檀木案上洇开一片深色水痕。
“什么时候的事?”
小太监伏地颤抖:“回、回陛下,就在半刻钟前,德妃娘娘身边的宫女去佛堂送茶,推门就看见。。。。。。”
萧玥指尖微微收紧,信纸在她手中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太巧了。
德妃早不自尽,晚不自尽,偏偏在吴司宝辨认出信笺材质的这一刻悬梁,倒像是被人掐准了时机灭口。
她抬眸看向弘德帝,父女二人目光相接,皆从对方眼中看出凝重。
“此事由内侍省、宫正司彻查,朕要知道佛堂里究竟供的是菩萨,还是魑魅!在真相大白前,别让朕听到任何风言风语!”弘德帝拂袖而去。
宋司正立于德妃尸身前,指尖悬于那道深紫勒痕之上,眉头微蹙。
“索痕斜向耳后,无挣扎痕迹,舌抵齿,睛突,确为自缢无疑。”她低声对身旁典正道:“颈侧针眼细查无异常,应是生前针灸所留。”
典正翻看德妃近日的脉案,点头附和:“太医署记录,德妃娘娘连日头痛,陈太医曾用金针疗法。”
太医丞以银针探喉,未见毒物反应。
“十指甲青黑乃尸僵所致,非中毒。”他捻须沉吟:“体表征候皆合自缢,无外力加害迹象。”
验尸完毕,宫正司女史随即为德妃殓容,在衣袖中摸出一封书信。
不多时,这份书信便被呈到了御前。
“妾以铁勒贱躯,蒙天恩入侍宫闱十余载,然夜夜惊梦,皆见漠北风沙。。。。。。
去岁腊月,妾知贤妃嫉恨皇后,遂假作梦呓于佛前,言太子已亡故。贤妃愚鲁,竟当真传讯至立政殿。刘氏死后,妾再命人送密信于二皇子,言明皇后之死另有真凶,本想激他暗中追查,与公主斗个两败俱伤。岂料竖子愚钝,大行鬼神之事。今事败露,妾当以命赎罪。唯愿陛下明察——此局自始至终,皆妾一手所布。”
弘德帝烦躁地拨弄着手中的手串。
“陛下?”李福安捧着参汤轻唤。
瓷盏被猛地扫落,参汤泼在遗书上,“贤妃愚鲁”四字顿时晕染成一片褐红。
“好一个‘一手所布’。”弘德帝低笑出声,“朕的妻子、妃嫔,倒成了你铁勒的棋盘走卒!”
弘德帝忽然想起十二年前——铁勒献女和亲那日,十六岁的德妃跪在丹墀下,红衣似火,眉眼间具是恣意潇洒,如今已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甚至姣好的容颜下不知道掩藏着什么。就连一向温良恭俭的崔贵妃,也不知是人是鬼。
弘德帝凝视着案上的遗书,指节叩在紫檀木上,一声声如更漏般沉冷。德妃之事事发突然,尚且不曾处置二皇子,眼下暂且动不得铁勒,便先处置了他。
“萧琅。”他缓缓开口:“身为皇子,不思进取,反以鬼神之事乱宫闱,按律当削爵流放。但念其年少丧母,心智昏聩,着禁足百福殿,无诏不得出。”
宫正司的刑房里,德妃的贴身侍女秋雯已被拷问三日,十指鲜血淋漓,终是撑不住,一五一十的全部招供了。
宋司正将秋雯的供词上呈。德妃之母乃前朝宁国公主,和亲铁勒,前朝国破后,便一直领兵骚扰大梁,直到弘德元年议和。遣女入宫,名为和亲,实为细作。至于为何自尽,一来东窗事发,德妃以自缢维护最后体面;二来,自她入宫,郑皇后怜惜她远离故土,一直照顾有加,结果她却害她性命,实在有愧。
“陛下。”她跪在殿中复命:“德妃一直以来都是铁勒的细作,和亲入宫是为了谋害陛下。只是苦无机会,这才害了皇后殿下。就连。。。。。。”
宋司正一咬牙,道:“就连太子殿下染病也非意外。”
去年颍州水患,弘德帝派太子赈灾,谁知竟染上了瘟疫,病逝于途中。原以为是天灾所致,没想到是有人处心积虑。
甘露殿的烛火彻夜未熄,弘德帝召集亲信大臣密议。
“诸卿可知,乌苏氏此毒妇,竟敢谋害储君,又刘氏之手害死皇后,朕恨不得明日便发兵荡平漠北!杜卿,户部现存粮草可支多少兵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