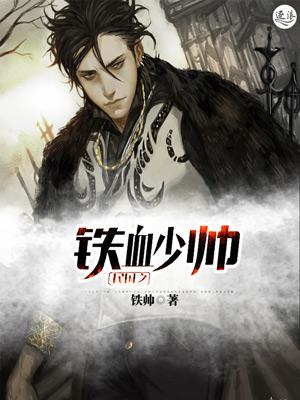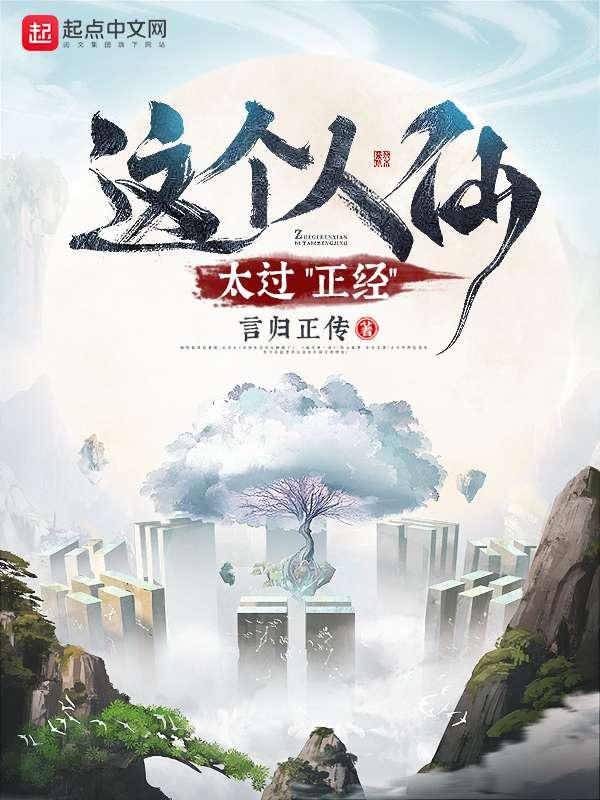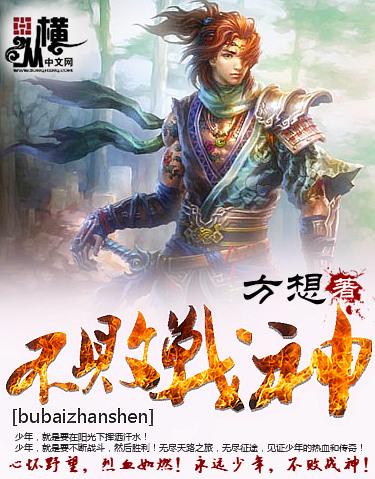鹅绒锁>她的字,我的戏 > 暗流与共谋 无声的战役(第1页)
暗流与共谋 无声的战役(第1页)
时间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中悄然流逝。
每周四下午三点,成了我(苏晴)生活中一个固定且……带着某种沉重期盼的坐标。我依然会提前陷入焦虑,依然会在去往姜医生诊所的出租车上胃部抽搐、手心冒汗,依然会在那扇木门前经历激烈的内心挣扎。
但不同之处在于,我知道门的后面,是一个被允许沉默、被接纳存在的空间。这认知像一块小小的压舱石,让我在恐惧的风浪中,不至于彻底倾覆。
在姜医生温和而专业的引导下,我像剥洋葱一样,极其缓慢地、一层层地尝试触碰那些被我深埋的痛苦。我们从最表层的身体感受,逐渐过渡到情绪的描述。
“……像……被困在……一个透明的……盒子里。”我艰难地组织着语言,声音低哑,“能看到外面……但……隔着一层……无法穿透的……膜。”
“盒子里的感觉是怎样的?”姜医生的声音平稳,不带任何评判。
“……安静……太安静了……”我蜷缩在沙发上,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沙发布料的纹理,“但……脑子里……很吵……有很多声音……在骂我……说我一无是处……”
“那些声音,听起来像谁?”
“……像我……自己……”说出这几个字时,我感到一阵尖锐的羞耻。
姜医生只是轻轻“嗯”了一声,表示听到了。没有惊讶,没有同情,只有平静的接纳。
这种接纳,让我有勇气,继续往下挖掘一点点。
我开始尝试在邮件里,向林夕透露一丝丝,属于“苏晴”而非仅仅是“原作者”的、与创作相关的情绪波动。不再是崩溃时的尖叫,而是一些更细微的、关于创作本身的情感。
比如,在回复她关于叶文婧某段内心独白的理解时,我会在专业分析之后,附加一句看似随意的话:
“写这一段时,窗外正在下雨。雨声让人……感到平静,也感到……更深的孤独。”
或者,
“有时会觉得,叶文婧的偏执,或许是我自身某种……无法安放的渴望的投射。”
这些话语,像小心翼翼探出触角的蜗牛,既渴望被看见,又随时准备缩回。
林夕的回应总是恰到好处。她从不深究我情绪背后的原因,也从不滥用同情。她只是精准地接住这些情感的碎片,将其融入对角色的理解中:
“谢谢苏老师。‘雨声中的孤独’这个意象,让我对叶文婧在寂静观测站里的状态,有了更具体的感受。我会尝试在表演中融入那种被潮湿和寂静包裹的质感。”
“无法安放的渴望……我似乎能触摸到一点了。这让我觉得叶文婧的追寻,不仅仅是理性的,也带着某种……悲壮的情感驱动力。”
我们像两个隔着一条汹涌激流的人,依靠着一条由文字和角色编织而成的、纤细却坚韧的绳索,传递着彼此才能理解的信号。
这种无声的、仅限于特定频道的交流,成了我灰暗生活中,一缕稳定而珍贵的光源。
然而,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
我(林夕)清晰地感受到了苏晴在邮件中那细微的变化。那些偶尔流露的、与她自身相关的情绪碎片,让我既欣喜又心疼。欣喜于她似乎正在尝试打开一点点心扉,心疼于这每一步背后,可能都伴随着巨大的艰难。
我将这份感知,更深地融入到了表演中。叶文婧在我身上,不再仅仅是一个被诠释的角色,她仿佛成了一个真实的、承载着另一个灵魂部分情感的容器。
这种投入,带来了表演上的突破,也引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关注。
在一场媒体小型探班活动中,几家关系较好的媒体被允许进入片场,拍摄一些拍摄花絮和进行简短采访。我和陈灏作为男女主角,自然是焦点。
大部分问题都围绕着剧情和角色。但当一家以深度报道著称的媒体记者将话筒转向我时,问题变得有些不同:
“林夕老师,我们注意到您在塑造叶文婧这个角色时,展现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非常内敛且有力量的表演风格。听说您与原作作者苏晴老师有非常深入的交流,这种表演上的蜕变,是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指引?您能谈谈这位神秘的作者吗?似乎她非常低调,几乎从不公开露面。”
问题很委婉,但指向性明确。现场瞬间安静了一些,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包括旁边看似随意、实则竖着耳朵听的陈灏。
我的心微微一紧。我知道这个问题无法完全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