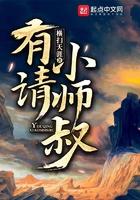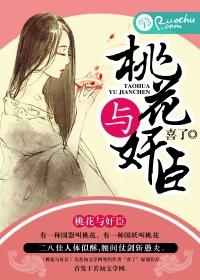鹅绒锁>天幕直播朕的恋爱史 > 吃火锅(第2页)
吃火锅(第2页)
这暖锅,是一种可以端上餐桌的锅,锅下面有足,中间有炉膛,可以放入炭火持续加热,在大晟又被唤作“古董羹”。其名由来,一说是因它乃沿用古法用来取暖和烹食的锅具,二说,便是因食物投入滚汤中会发出“咕咚”声响,故而谐音得名。[1]。
黎昭第一次吃暖锅的时候,便眼前一亮——这不就是令他魂牵梦萦的火锅么!只是吃法不太一样,有点像单人小火锅。
只是大晟的吃法颇为“豪放”,将食材一次性全部投入锅中烹煮,没有涮吃的习惯,而且没有蘸料,汤底也多是清淡高汤,于他这无辣不欢之人而言,终究少了些滋味。
是的,黎昭准备用火锅招待明臻。只是黎昭个人喜欢比较热闹一点吃火锅,于是开府后,他亲自画了图样,命人特制了一口更大的暖锅,更在中间加上一道巧妙的隔板,做成了独一无二的“鸳鸯锅”。
自此,这口锅便成了他解馋的利器,招待的最多的还是明臻,当然也有一些他的纨绔朋友们。
唯一可惜的就是辣椒还没有传入大晟。在他的船队回来前,他只能退而求其次,以花椒、茱萸、生姜与胡椒调和,勉强模拟出几分辛辣,不太过瘾。
如今在民间也有流传这样的吃法,只是能够欣赏这个辣味的人不多,譬如明臻,一吃辣就上脸。
他还记得第一次怂恿明臻尝试时,这位向来风度翩翩的世家公子被呛得眼角泛红、咳嗽连连,平日里的从容荡然无存。许是那次留下了“阴影”,自此之后,明臻便彻底与辣锅划清了界限,坚定地守在清汤一侧。
酉时正,客人踏着月色与梅香,准时赴约。
“殿下。”明臻于亭外站定,从容一揖。
黎昭从思绪中回神,笑着招手:“就我们两个,还讲究这些虚礼做什么?快进来坐。今儿吃暖锅,这两日在大理寺对着成山的卷宗,看得我头晕眼花,必须得靠这口锅子回回血。”
“礼不可废。”明臻步入亭中,在他对面坐下,语气温和却坚持。
黎昭一挑眉,双手支着下巴,故意歪头看他,开始翻起旧账,“这么说的话,你以前跟在我后头一口一个‘小娘子’,教训我这也不可为、那也不许行的时候,怎不说礼不可废?一口一个阿昭的时候,怎么不说礼不可废,现在跟我论起礼来了。”
他做恍然大悟状,眼中闪着狡黠的光,“哦——原来这礼数周全与否,全在明哥哥的一念之间啊?”
话一出口,黎昭自己也顿住了。“明哥哥”这称呼,是幼时初识时的称呼,如今骤然脱口,竟觉得有些烫嘴。
“停。”明臻出声,耳根微不可察地泛红,执壶为他斟了杯热茶,算是讨饶,“阿昭,我认输。”
黎昭看着对面明臻微红的耳根,故作镇定,“罢了,本殿下大人有大量,不与你计较。”
随即挥退左右,“你们都下去吧,自去暖阁里也支一锅,这里无需伺候了。富贵,带风源一同去。”
“是,谢殿下恩典。”侍从们含笑退下,亭中顷刻间安静下来。
此刻彷佛只剩下这桌案之间,一轮月,两个人,以及点点梅香萦绕其中。
黎昭觉得该说点什么来打破这过分的静谧,轻咳一声:“咳,那什么,明相后来,没罚你进祠堂吧?”
明臻正执箸将鲜切的薄羊肉放入清汤一侧,闻言动作未停,只抬眼看了看他游离的眼神,顺着他的话说了,“没有。阿昭神机妙算,信来得正是时候。”
“真的?那就好。”看刚才明臻行走间,动作如常,应是无事。毕竟现在长大了,再扒明臻的衣服不太好,明臻会跟他翻脸的。
“嗯,”明臻应了一声,将烫好的羊肉夹到他碗中,“阿昭这两日在大理寺,查得如何?”
“唉,别提了。”黎昭立刻苦了脸,“卷宗堆积如山,看得我眼睛都快瞎了。”他放下筷子,神色认真起来,“正好,有件事我想不通,要问你。”
明臻停了箸,专注望向他:“嗯?”
“你说,天幕讲述的这桩案子,为何到了庞迎这里便戛然而止?按我们暗中查探,楚王扰乱科场绝不止近两届。难道……天幕里的那个‘我’,竟未能查个水落石出吗?”
“阿昭,无论哪个你都是你,核心都不会变。但你是否想过,将所有的黑暗与污秽彻底公之于众,真的是最妥帖的做法吗?”
“什么意思?”黎昭语气不由得带上一丝急切,“若不公之于众,那些往届蒙冤的学子怎么办?他们的公道谁来偿还?”
“我明白你的心情。”明臻的目光透过蒸腾的白雾,显得格外深邃,“制定此计之初,我虽知民意可用,却也未曾料到其力量竟能汹涌至此。”
“如今,天幕仅揭露两届黑幕,其中一届甚至尚未发生,已引得朝野震动,民情沸腾。若将历届积弊一并掀开,告诉天下人,科场舞弊并非偶发,而是盘根错节的常态。。。。。。阿昭,你想过学子们会如何想?天下百姓又会如何看吗?”
他稍稍前倾身体,语气凝重:“寒窗苦读的士子,将不再相信科举的公正。他们会想,既有一个楚王,谁能保证没有第二个、第三个?届时,朝廷取士之根本被动摇,国家将如何选拔栋梁?”
“而黎民百姓,在一次次冲击下,会对朝廷彻底失去信心。更可怕的是,若有不轨之徒借此煽动,宣扬‘朝廷无道’,届时人心浮动,社稷倾危,后果。。。。。。不堪设想。”
明臻一顿,接着道,“我们求的是革新除弊,拨乱反正,而非。。。。。。颠覆一切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