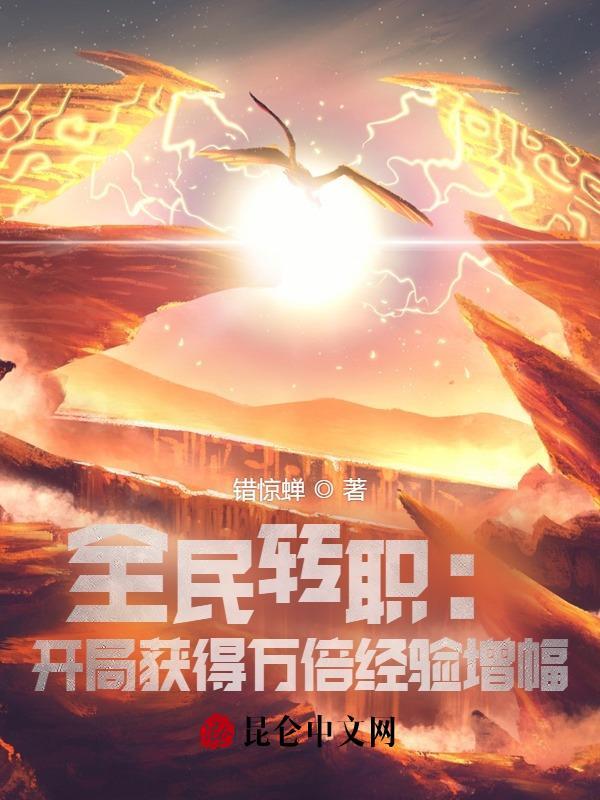鹅绒锁>小病秧子养护指南 > 7080(第6页)
7080(第6页)
“我跟他说了,早点解决。他不知道在做什么,硬是拖着!这件事对他的影响他自己心里没数吗?还有他的家里人,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管不顾?”
“说来我就气,还有上次科技杯,我们准备了整整一个月,他本来是要拿奖的呀!是要拿奖的!”老教授再一次把桌子敲得“邦邦”作响,“那个奖他要是拿到,日后路就好走了呀!是他以后的敲门砖!含金量比他之前参加过的其他比赛都要高!结果临到头,他跟我说不比了!”
老教授说到这里,激动得拓沫星子乱飞,“我当时问他,说他要是有什么困难,说出来,老师帮着他一起解决。这小孩子死活不开口!跟我说不比了,要回去。”
隔壁老师闻言,也插了一句,“盛恪啊,不知道翘了我多少堂课。要不是童教授您看中他,我高低得关他一门。”
老教授重重一叹气,这会儿更像是唠家常,说起家里那个不争气的孩子,有满肚子的苦水要倒,“什么都好,就是闷得要命,锯嘴葫芦!这叫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我也不好评判。但这么优秀的孩子,家里应该全力支持的呀!”
“还有这次,他拿到优营名额,我都准备好亲自带他。结果他说他要回去。我真弄不懂,人家挤破头想要的名额,他说放弃就放弃,他家里到底什么情况,需要这个孩子做到这个地步?”
“但我听说,盛恪填的政审材料,不是和父母都不联系?”
老教授摇头,又是一阵唉声叹气。而后才想起来自己眼前还有个人,“你还有什么要问?”
傅渊逸咽着干涩的喉咙,笔尖在笔记本上留下不可控的墨点,“教授,或许您知道,盛恪的身体是不是不太好?”
老教授想了想,“是看他吃过几次药。”
“我在医院碰见过他两回。”另一个老师说,她老公是医生,所以往医院跑的次数很多,撞见过盛恪。“一次挂水,一次他好像是去做胃镜吧,就上个月。”
“家里有人陪?”老教授立马问。
“倒是没见。胃镜是另外一个男孩子陪着的。因为要全麻嘛。”
“你看看,你看看!他家里连孩子的身体都不关心。”老教授痛心疾首,“盛恪家里拖累他太多了呀,太多了……”-
同一时间,上海。
“陈先生。”
“阮医生。”陈思凌冲对方点头致意,然后跟着阮医生进入诊室。
“好久不见。”
凌遇刚走的时候,阮医生也曾是陈思凌的心理医生。
“我这次来,是想问一下傅渊逸的情况。”陈思凌开门见山,“我知道,小东西的情况不太好了,但我想知道,他现在到了哪个阶段。”
阮医生沉吟片刻,道:“我们前几年一直控制得不错,盛恪加入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稳定。”
陈思凌颔首,“盛恪来了之后,傅渊逸确实都是他在照顾。”
“小逸的情况是在今年夏天急转直下的,但原因……我也无从知晓。我对他进行疏导的时候,他下意识地避开了,所以我猜测,应该也和凌先生有一定的关键。”
陈思凌蹙眉,“这段时间没有发生过什么。这一点,我和盛恪讨论过,可以确信。”
所以,他们至今不知道,点燃引信的那个事件到底是什么。
陈思凌神情愈发凝重,“我们下一步能怎么做?”
他和阮医生都知道,傅渊逸创伤后应激的触发事件是凌遇,但PTSD的创伤后再体验、惊恐,并非必须要经历明确的事件才会触发,也有可能是某个细微的场景,甚至只是一个相似的气味,例如汽油、柏油马路的沥青味,或者一段声音,例如急刹车,金属摩擦,都会导致傅渊逸的情绪波动,从而触发傅渊逸的压抑记忆。
“我想,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设法稳定小逸的情绪。药物治疗我会按照他的情况继续调整计量,先稳住他的睡眠和焦虑。”
陈思凌抬眼看向他,表情并不好。
阮医生当然知道他不想听到这样笼统的、没有明确治疗方案的回答,但是——
“小逸现在处于防御机制非常强烈的状态,强行追问只会激起他更大的抵触情绪。我们必须谨慎的去建立他的安全感,创造足够稳定的环境,帮他重新建立表达,而不是极端的回避。”
“这样我们的治疗才能继续。”
“另外,这次情况突然的恶化,会拉长他的治疗期。”阮医生语气低缓却十分清晰,“当然,我不希望他进入终生的慢性病程,但以现在的情况看来,我想您和盛恪需要对此有心理准备。”
“还有,我希望您能同意近期安排小逸进行更密集的心理疏导。我想尽可能缓解他的防御姿态。”
陈思凌点头:“自然。”
“在这段期间,您和盛恪也要足够耐心才行,他应该很需要你们。”
走出医院,陈思凌问司机要了支烟,站在路边抽。
他戒烟很久了,大概能追溯到他还在追凌遇的时候。他痞,而凌遇一看就是三好学生。
为了追三好学生,他乖乖把烟戒了。
当然一开始也没那么好戒,心情一不好还是习惯性地想来上一根。